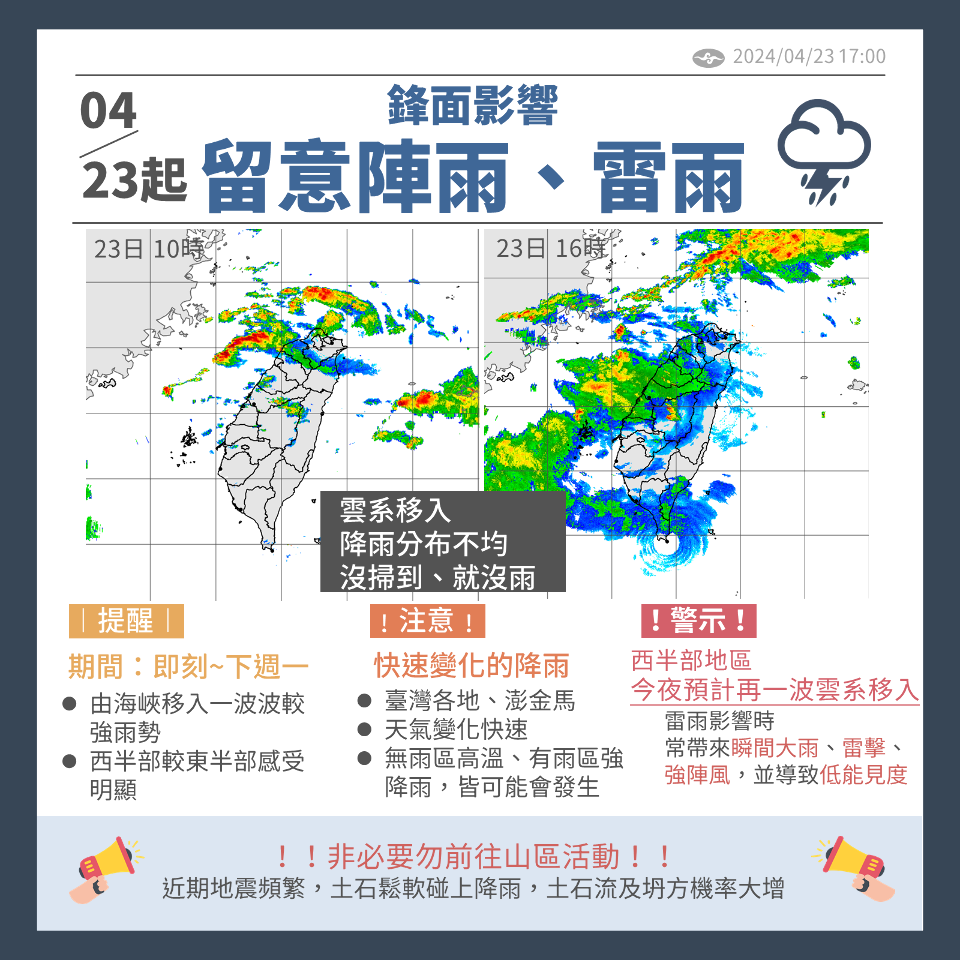三月。濛濛細雨。台北。西門町的巷弄。
我和朋友坐在「飛地Nowhere」屋簷下的木凳上,等著下午一點鐘的開張。
「飛地Nowhere」是一家香港有志的文化人開的獨立書店,香港社群在台灣的文化「在場」。
玻璃門外的兩層簡易開放書架,隨意擱著一些二手書。有標價,書費隨意擱置。
在這裡,一本有點兒泛黃《絳紅色的地圖》,帶我遇見1998年的唯色。
這是唯色尚在體制內當《西藏文學》編輯時的一本旅行記。
一九八一年,唯色從藏東的康定初中畢業,考入西南民族學院(成都)預科班,九年後回到拉薩。
而拉薩因為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抗暴活動,正經歷了北京對拉薩實行的長達一年零七個月的軍事戒嚴。
拉薩?拉薩!
回歸拉薩的唯色,連「拉薩」這個詞的藏語都發音不準,被親戚們笑言舌頭是「做過手術的舌頭」。
「我是誰?」為何成為「一個不倫不類的人」。血緣或骨頭,藏地。漢地。夾著康巴口音的藏語與四川口音的普通話。旁觀者?過客?觀察者?獵取奇異俗風情的攝影者?亦或,故鄉,血統?
很多年,唯色曾困惑於「故鄉」、「血統」這些概念。百分之幾的藏人血統,百分之幾的漢人血統。似乎必須用「學術」與「科學」的精密儀器放在顯微鏡下檢測其含金量。
「猶如置身於一塊狹長的邊緣地帶,溝壑深深,道路彎彎,且被驅散不盡的重重迷霧所籠罩,難辨方向。而終生踟躇在這一塊邊緣地帶,這本身就已經把自己給孤立起來了。這邊的人把你推過來,那邊的人把你推過去,好不容易站穩了,舉目四望,一片混沌。多麼難忍受的孤獨啊!猶如切膚之痛,深刻,又很難愈合」。
七歲以後,唯色接受的學校教育全部是漢語教育。名為「民族學院」的學校,從未有過實質性的民族教育。巧合的是,本書封對唯色的介紹,將「西南民族學院」印成「西南名族學院」。無心誤字,抑或有意警示那人人心中皆知的事實—「民族」早已有名無實,成為「名族」。

「民族學院」誤字為「名族學院」,歪打正著。
曾經使用漢名「程文薩」女孩,甚至自己還取過漢化文藝腔「程雯莎」這個名字,《紅樓夢》裡的「晴雯」的「雯」,「莎士比亞」的「莎」。
回到拉薩後,那無所適從的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換上了父親起的藏名—茨仁唯色。茨仁唯色-永恆的光芒。從最初的啼哭中,從第一口乳食中,認出隱喻的文化臍帶,血脈的根源。從此,這盞長燃不熄的供燈,住著她的故鄉,她的靈魂。她的親人,她的夢想,她的喜悅和她的哀傷。
光芒在上,西藏在上。
人,往高處走。
「我的一生都是被置換的一生。母語、習慣、記憶、水土、家鄉、甚至容貌。連五蘊(佛語),一切的一切都被置換了」。但,就像被換血,但從未換心。

唯色與她的故事大王的母親。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在大昭寺遇到尼瑪茨仁。
唯色多次描述過這位「喇嘛導遊」。文雅,謙和,平靜,自律,自重。「一雙細長如壁畫中的佛眼裡含著一片安詳」。
尼瑪茨仁擁有淵博的知識和智慧。
當有人譏諷風餐露宿、爬山涉水,一路行五體投地之禮,朝聖到心中的聖地拉薩大昭寺的藏人是「自虐式的苦行」時,他告訴那些外來的「觀景者」:為了尋求內心的寧靜和解脫,肉體上的磨難不算什麼,而那些看上去體面又風光的人,內心卻不潔淨,不光明,那才是真正的苦。而寧願沉溺其中,卻從不思考解脫之道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殘忍。
一九九八年之後的一年,尼瑪茨仁作為「翻身農奴」,作為「被解放的」藏人的象徵,被選上代表西藏去挪威參加了一個關於人權的國際會議。
是的。尼瑪茨仁有很多重要的頭銜。其中一個是拉薩市人大常委。
挪威,就是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那座北歐城市。
在那裡,尼瑪次仁遇到他異鄉流亡的同胞在抗議。
「加米(漢人)」、「共產黨喇嘛……」。
「他的西藏喇嘛」僧侶的袈裟如烈火燃燒。火焰灼燒他藏人的身體,藏人的心。更何況火上澆油火更猛。那一個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飛濺的油,是飛濺的融化的滾燙的酥油。尼瑪茨仁他低垂的頭顱,彎曲的脊背,蹣跚的雙腿,被一滴滴飛濺而來的酥油深深地燙傷了「。
尼瑪茨仁在國際會議上背書。那些有教養的西洋聽眾仿佛都知道他的難處,知道他在背書,也不為難他。
只是,當他的流亡同胞握住他的手,哭著請求他不要回去,「古修(對僧侶的尊稱),你跟著這些中國人做什麼,你是藏人啊,記住你是藏人啊」。
「那是我們的家鄉啊,都走了,把它留給誰呢?」尼瑪茨仁的眼淚奪眶而出。
一瞬間,尼瑪茨仁也閃過一絲不跟「他們回去」的念頭。但,那只是一瞬。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當飛機從奧斯陸的機場慢慢升起,漸漸地離開這個象徵自由的國家,兩行熱淚悄悄地滑下了尼瑪茨仁瘦削的臉頰」。
唯色執筆之手,十分節制。然而,尼瑪茨仁內心深邃的隱痛,在喧嘩的寂靜中生長,又融化於雪山,雪地、岩石,融化於月亮的靜脈和太陽的骨骼中。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深深地陷入一種宿命似的幻覺之中」。神奇而潔白的哈達般閃耀的光,刺痛她的皮膚,又照耀著她啟程,在雪域的路上。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遇見比她的年紀小得多的阿尼。她們正徒步回到自己的寺院。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遇見一位矮個子阿尼,強烈的陽光下戴著一頂難看的毛線帽。
「當她沿著帕廊,邊走邊喊,那藏人皆知的口號,就被衝上來的便衣蒙住嘴巴」。
「換一頂布帽子吧」
我打算送給她。
但她不肯。「我頭疼,戴毛線帽要好受得多」。
為什麼?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的頭,在監獄裡被他們打壞了。」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遇見丹增和他的兒子。
丹增,曾是一位受萬民尊敬的「仁波切」。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那場巨變中,十四歲的他,和他的三位兄弟一道,護衛並跟隨尊者逃亡。途中失喪了親人,失喪了經師。並隨廣大農奴「翻身解放」。他隱名埋姓,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歷經文革,歷經改革開放。而他的兒子,比他佛緣更深。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懷抱人世間最美麗的花朵,趕在凋零之前,熱淚盈眶,,快快奔走只為獻給一位絳紅色的老人,一塊如意瑰寶一縷微笑,將生生世世,繫得很緊。」
一九九八年的唯色,已經清晰地為自己的寫作方向定位,那就是做一個見證人,看見、發現、揭示,並且傳播那秘密-那驚人的,感人的卻非個人的秘密。像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一樣,說出故事,用記憶對抗遺忘。

2011年得不到護照的唯色通過互聯網見到了尊者達賴喇嘛。
一九九八年後的又五年。唯色在中國南方的出版社出版出版了散文集《西藏筆記》。書中寫了尊者是「所有虔誠的藏人最熟悉、最親切、最渴望的人」。而其中的《尼瑪茨仁》,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唯色被中央統戰部定性為「犯了政治錯誤」,被解除公職,不得不離開拉薩。
《絳紅色的地圖》曾帶唯色走過雍和宮,那座位於帝都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一九九八年後的又八年。夏日的晴空下,唯色帶我走過。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一個小時候用七种彩色的紙條糊在兜兜上,用彩色的毛線與頭髮混成長辮子,蹦蹦跳跳《洗衣歌》的南方漢人女子,見到了一位佩戴瑪瑙的耳環,手上帶著銀飾的美麗的藏人女子。
仿佛前世的舊相識,在熙熙攘攘的萬事萬物中,也能認出彼此。
我急急似乎有許多話要說。比如,我在北歐聽到的詩《雪山和雪山人》,比如,台灣出版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比如,我一生從未到過的西藏,唯色如何表述?……。
然而,我們只是手牽手慢慢地走著,並未談更多。
風,像魚兒一樣溜溜地,從我們身邊游走。
那以後,又過了快十七年。
這些年間發生了許多的事。
二〇〇八年三月,藏地的抗議,改變了許多人,也改變了唯色。她放下了手中的寫作計劃,成為一名當代西藏的記錄者。她像一個無畏的孩子,說出許多人不敢說出的真相。她記錄了藏地發生的種種悲傷,記錄了每一位自焚者的名字。
我遠在千里萬里的東瀛,每每深夜讀她那些痛苦的文字,想像著每滴「滋滋」飛濺的火苗該是怎樣灼傷她的心,她又該以怎樣的堅韌和哭泣來化作筆墨。
當局攻擊她的部落格。甚至數度警告她將無緣無故地「被失蹤」。
她仍只是寫,《殺劫》所揭示的西藏文革,已被更激烈、更當下、更切迫的現實所替代。

一九九八年後的又十七年,唯色又出版了《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增訂修改版。
我數了數,大約修改了兩百四十三處文字,增加了二十多張寫真。
比如,舊版的「拉薩事件」,改為新版的「拉薩抗暴」;又比如,舊版的「碉堡」,改為新版的「碉堡,建成於五十年代,位於今天的賽康商場對面。當時解放軍在拉薩城裡建有多個碉堡,藏人並不知道是干什麼用的。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抗暴’期間,解放軍把玻璃門窗戶推開,露出機關槍,這石頭就成了軍用碉堡,打死過很多藏人」。又比如,舊版「也深深觸及藏人的靈魂深處」,新版改為「如此顛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於連根挖去一個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觸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們貧困交加;所觸及的更是藏人的靈魂,使他們在喪失傳統和信仰的時候,內心分裂,魂無所繫」。
唯色認為,這些修改,表明的不只是一種民族認同感的深入,還是一種對遭到大一統以及中共意識形態長期洗腦所導致的某種內化的覺醒及修正,這不是簡單地用詞上的修訂,而是一種個人的反抗。通過語言,反抗語言。
一九九八年後的唯色,又在台灣出版了很多書。
幸有台灣。只有台灣。
唯色的寫作理念,從「寫作即遊歷」,深化為「寫作即流亡,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
絳紅色的地圖,帶唯色看見西藏現代歷史上那些緊閉鼻孔的生者和死者。
唯色帶我看見,看不見的西藏。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