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國中時,我的教室右邊是一排A段班,左邊是一排B段班,我的教室剛好就在中間。我國小就是舞蹈班,本來日子是很單純的上課、跳舞,但因為有天到B段班旁的廁所上廁所,結交了一群不一樣的同伴,然後從吸菸開始,後來吸毒、械鬥,被抓進警局,變成觀護少年。
對我來說,那段日子,就像是進入了一個「神祕世界」裡。
今年(2023)是雲門舞集成立50週年,3年前,我從林懷民老師手中接下雲門舞集藝術總監的棒子,沒多久就碰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考驗,同時間也有不少人好奇我如何在林老師斐然的成就下,繼續帶領雲門往前走。其實,我跟林老師的成長背景天差地遠,無法比較也不能複製;我所能做的,就是持續用自己的方式編舞,用肢體與觀眾對話,讓觀眾感受到舞蹈的力量。就像我年少時曾經吸毒,走上岔路,最終把我拉回來的,也是舞蹈。
跳舞,讓過動的我如魚得水
我從國小一路念舞蹈班到大學,但是小時候會念舞蹈班,純粹是因為我太「過動」。小時候到哪都像個「破壞王」,連帶也常掛彩。比如去公園玩旋轉器材,不知怎麼地差點削去耳朵;到溪邊玩水,大拇指差點被碎玻璃割斷;還有一次跟著媽媽去美容院,我在一旁玩刀片,不小心切掉一塊肉,媽媽顧不得頭上還有髮捲,急急忙忙帶著血流如注的我衝去醫院急診室⋯⋯諸如此類因過於活潑好動所引發的大小意外,是我成長過程常見的插曲。
就這樣「跌跌撞撞」到小學三年級時,學校發了一張單子,上面畫了兩個格子,一格是資優班,一格是舞蹈班,要大家報名。雖然我成績也算不錯,但還是很有自知之明地,把自己的照片剪下來貼在舞蹈班的框框裡,就這樣交了出去,也順利考上。媽媽知道後不僅沒反對,還很贊成,大概也是覺得跳舞可以消耗我很多體力吧!
舞蹈班的生活,不用一直坐在教室裡,對我來說簡直如魚得水。跳舞,其實就是透過身體去展現自己的想法,就像有堂課是即興創作,老師會出題,像是海浪、風等,讓我們用身體去表現,我就恣意想像,擺弄身體,其實不曉得自己在跳什麼,但就很開心。
回想起來,在舞蹈這條路上,我好像不用經過太多努力就可以當上主角,經常是受到矚目的那一個,可能是我身材比較高,具有天生的優勢吧!
有些家長可能會反對男孩子學跳舞,不過我那一屆很特別,班上有9個男生,一次排開很有氣勢,也比較少招來異樣眼光。但我弟弟就沒這麼幸運,他也念舞蹈班,但他那屆男生不多,常有其他男同學嘲笑他是娘娘腔,這些指指點點和歧視讓他壓力很大,國中舞蹈班沒念完就轉到普通班了。
紙箱裡聆聽世界,創作出《十三聲》
我跟弟弟學舞蹈,我還有一個姊姊學鋼琴、學聲樂,但是我爸媽沒有藝術背景,也沒有高學歷,一個國小沒畢業,一個國中沒畢業,他們雖然沒有給我們很多知識上的教育,但他們的教養方式是民主開明的,支持我們發展興趣。媽媽對於我們的關愛也溢於言表,她不管多忙,每天一定會早起做早餐,中午幫我們帶便當。
父母在萬華(舊稱「艋舺」)擺路邊攤賣鞋,養大我們3個孩子,有陣子李登輝當台北市長,大力推行早安晨跑活動,爸媽就帶著我們四處擺攤賣布鞋,生意正忙的時候,就把我跟姊姊擺進一個大紙箱裡,然後在裡面放了一些玩具、拖鞋和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的世界就是紙箱,和從那望出去的方形天空。
我常常一邊看著頭頂上的方形天空發呆,一邊聽著街頭傳來的各式聲響,大人們做生意吆喝的聲音,或者是談論親戚朋友間的恩恩怨怨,默默地在心裡編故事。艋舺街頭裡廟宇和巿街斑斕繽紛的色彩、巿井和角頭生猛的肢體動作和語言,一直鮮活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有回發想新作品前,和媽媽談起艋舺生活的喧鬧往事,媽媽和我講起,60年代的艋舺街頭,有個真正厲害的傳奇人物叫「十三聲」,可以忽男忽女、幼聲老嗓,不管是古今佚事、流行俚俗,到他手裡,都是眾人圍觀搶看的好戲,讓我大感驚奇,我也以媽媽口述的故事,創作出《十三聲》這齣舞碼,一方面也希望,能讓父母輩的生命記憶,透過舞作傳遞下去。
成為安毒滲入校園首篇報導的主角
升上國中後,有些事情變得不一樣了。那時適逢台灣股市上萬點,「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爸爸擺攤做生意的時間變少了,經常泡在號子裡,不見人影。
那時,我的教室右邊是一排A段班,左邊是一排B段班,舞蹈班剛好在中間,全班有20來個同學,只剩下4個男生。
因為廁所在B段班那頭,我自然跟B段班的同學變得比較熟,我們會在廁所廝混,玩耍聊天,跟他們在一起時,言語和肢體都比較不受拘束,覺得很自在。後來也學會抽菸,抽著抽著,開始抽起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像是安非他命。漸漸地,開始翹課,翻圍牆出去,有時打電動玩具,有時去撞球;為了展現義氣,兄弟一吆喝,就去別的學校堵人。當時不曉得這些事情的嚴重性,只覺得非常好玩,就像有一個神祕的世界,等著我去探險。
國二升國三那年,學校安排畢業旅行,我跟一位同學計畫好要帶一些「違禁品」去,那天去他家拿貨,我一進門,就被幾個彪形大漢壓在地上,他們搜到我皮夾裡有一張鋁箔紙,旋即把我押進一台黑色廂型車,門一打開,我的好朋友全在裡面。有些人面無表情,有些人則是淚流滿面,我也是那個淚流滿面的。當下才驚覺,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我不是在玩遊戲嗎?為什麼突然變成真的了?那些兄弟間有趣的事情、刺激的冒險,突然變成殘酷恐怖的現實。
廂型車載我們去寧夏夜市附近的少年隊,那裡的建築物現在已經變成古蹟了。我記得車子從一處拱門那裡開進去,我們被那些叔叔們一一帶開,分別詢問。我哭著跟警察說,拜託不要跟我爸媽講⋯⋯。
我們被抓的消息隔天刊登在報紙上,大大的標題寫著「安非他命入侵國中校園」、「國中生吸食安非他命,鄭X龍」。我記得,那還是台灣第一次出現安毒滲透到國中校園的報導,所以整個社會非常震驚,原來全民瘋股市的同時,我們的學生已經沉淪毒海。我本來都是在舞作中擔任「主角」,這一次卻成了社會新聞裡的「主角」。
植物人安養中心震撼的那一幕
吸毒被抓後,因為我未成年,被判處3年保護管束,平時照常上舞蹈班的課,但每週六、日都要去法院報到,聽整天枯燥的演講,寫心得報告。還好那時我遇到一位非常好的觀護人,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盧蘇偉,他會盡量找機會帶我們脫離枯燥的演講,去植物人安養中心、孤兒院、療養院服務。通常我是負責去跳舞的那一個,我只要把腳抬起來,大家就笑得很開心,彷彿我是珍奇異獸般。我也樂得用我擅長的肢體語言跟大家打成一片。
我記得在創世基金會看到一位院民,他10幾歲就出外做工,不幸觸電,就此成了植物人。他的床位旁有一扇窗,看出去就是台北車站的屋頂,我一邊幫他翻身,一邊想到他的際遇,他躺在那裡已經10幾、20年了,無法動彈、不能言語,而我好手好腳的,怎麼會讓自己的人生走到這裡?那一幕深深觸動了我,多年以後,我還是會常常會回到這個瞬間,回到這個畫面。
後來,B段班那邊我再也沒去過,那些一起玩的朋友也徹底與我的生活隔絕,學校好像設了一個無形的柵欄,讓我再也碰不到曾經的兄弟。我已經不記得他們長什麼樣子,有時也會想到,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
我不確定這段經歷對我有多大的影響,不過國三那年的畢業舞展,我主動爭取編舞,前半段設計了一些很難懂的動作,展現出痛苦、掙扎的意象,配樂也比較抽象,到了某一個橋段,動作變得比較外放,配樂曲風也丕變,我選了林強唱的《春風少年兄》,音樂一下,整個板橋文化中心所有的觀眾都瘋了,他們拍手、歡呼,場面就好像是浪子回頭的一個高潮,值得慶祝的一個時刻!
那一刻,我結結實實感受到舞蹈帶給我的滿足,我喜歡舞台,我也愛掌聲,渴望受到關注。年少的荒唐,跟兄弟們混跡街頭的日子,就此成為舞台的背景,逐漸淡去。
脊椎受傷,從舞者退居編舞者
高中我就讀華岡藝校舞蹈科,畢業後考上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夜間部,此時遇到另一位生命中的貴人,已逝的雲門舞者羅曼菲,她知道我喜歡編舞,鼓勵我考轉學考,進入台北藝術大學。不過,大學四年級那年我又陷入迷惘,不知為何要學舞,終日沉迷網咖,決定休學先去當兵。因為站哨時常感覺全身酸痛,去醫院照了X光,醫師說我脊椎骨的椎弓已經裂了一個大縫,可能是過去跳舞前我不常暖身,興致一來就跳,長年累積下來的傷害。
我動了手術,把這個裂縫補起來。手術後穿著鐵衣,在家躺了好幾個月。爸爸本來希望我跟著他去賣鞋做生意,不要再跳舞了,但我發現自己還是對跳舞有熱情,努力說服他讓我回到北藝大,把最後一年的課上完。
畢業後,那時台灣唯一付得起舞者薪水的職業舞團就是雲門舞集,為了讓爸爸安心,我決定去考,也順利考上。在雲門那4年,衝擊很大。以前的我不愛唸書,但雲門每次出國表演都會帶一個裝滿書的箱子,讓舞者自由取閱;加上經常到世界各地演出,這些經歷讓我視野大開,心靈也有所成長。
然而,4年下來,我自覺受過傷的脊椎終究還是無法負擔這麼高強度的職業舞者生活,只好在萬般不捨下離開雲門。但我還是持續走在舞蹈這條路上,自己創作、編舞,接一些案子。那時羅曼菲老師擔任雲門2的藝術總監,邀請我編舞。那支舞作演出時,跟《春風少年兄》一樣,台下的觀眾反應熱烈,都嗨翻了。所以我又到雲門2從事編舞、創作,甚至出國比賽,一路到現在。
會跳舞是非常幸福的才能
我接下雲門藝術總監不久就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國內實施三級警戒,大家不能聚在一起,我跟舞者們只能透過視訊遠距教舞、練舞,這樣的變化讓我思索許多,深刻地感受到,原來,遠方的一個噴嚏,也會影響到這邊的快篩;地球另一端的戰爭,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糧食,世間所有的事情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好像有無形的能量在傳遞,在互相影響。這除了是我目前正在創作的新舞作《波》的靈感來源,也好似我狂放的年少時代,很多事情它就是發生了,也許沒有明確的理由,因為個性或者命運, 一些無形的「波」,促使我走進岔路,又幸運遇到貴人,引領我走出迷途,發現自己最擅長也最熱衷的,仍舊是舞蹈。
常有人問我,跳舞這麼辛苦,我又受過傷,為什麼會想堅持下來?答案其實很簡單,除了跳舞,其他的事我也不太會。我覺得身體是老天爺給我們最棒的禮物,會跳舞更是非常幸福的才能,因為我們不太需要外在的物件,就可以創作出許多可能,舞蹈其實也就是生命本質的展現。
我一直都有一個強烈的慾望,就像國三那年編的《春風少年兄》,音樂一下,眾人嗨翻,那種熱烈的回響是激勵著我持續編舞、持續創作的動力,這也是我唯一在意的事,其他都不重要。
我想和14歲的自己說⋯⋯
那時候的我,為了買毒品,偷父母的錢,甚至為了湊錢,欺負比較弱小的同學。
我想跟14歲的自己說,一個人永遠都不應該「傷害別人」,那是錯的,是很不應該的。至於年少輕狂走過的那些路,我覺得沒有必要談後不後悔,人生再一次,也許我還是可能走上那樣的路,但傷害別人是不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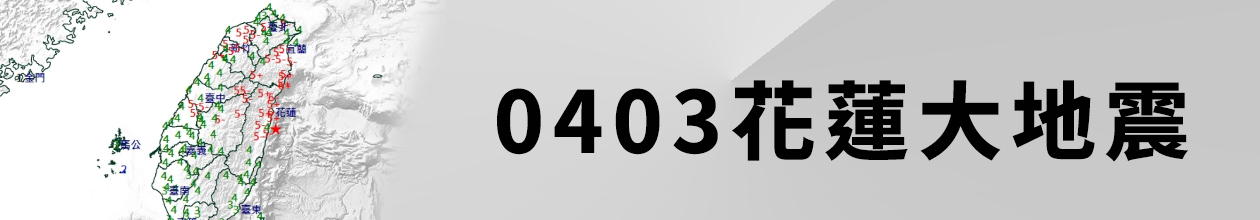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ti 中央廣播電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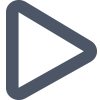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