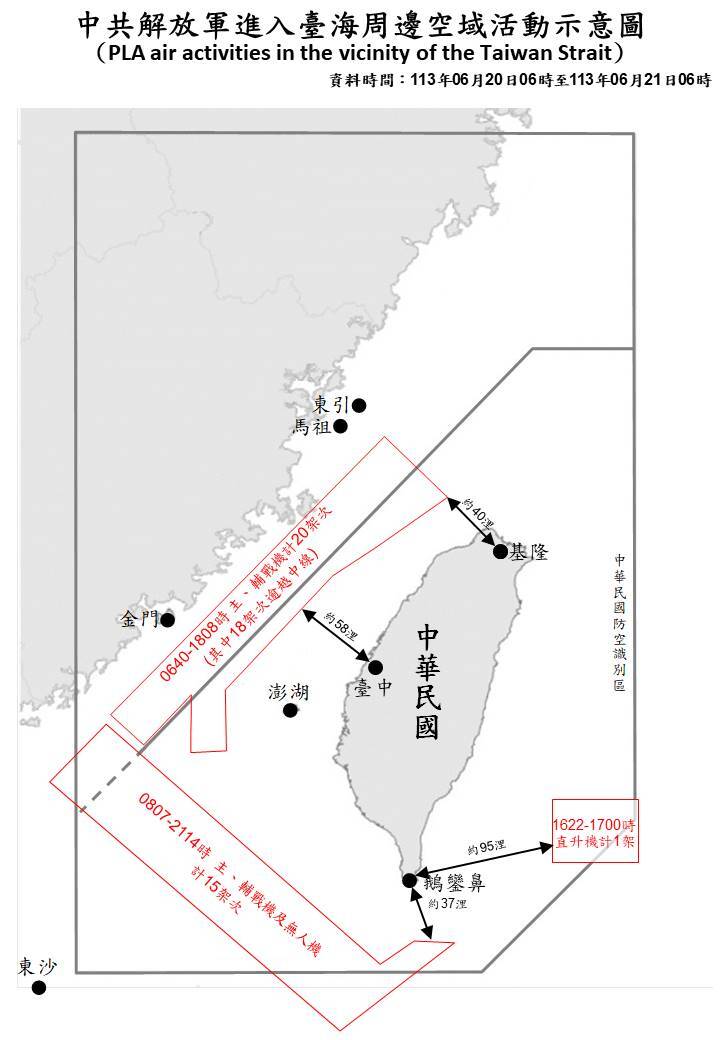作為一位流落在台灣的香港倡議者,許多本土/離散在別國的香港朋友都在上星期開始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場的群眾沒有像十年前一般衝進立法院議場?」甚至,「為什麼現場會出現如此多衝就是送頭、就是鬼!的論述?」筆者希望略略分享我的觀察,嘗試為這條問題增添一個可行的解釋。
在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在大規模街頭抗議之前,其實「公投護台灣聯盟」(公投盟)和「黑色島國青年」(黑島青)等團體早已發起過(相對)激進的抗議。他們在317晚突然衝進議場之前,已先試過以數十人衝進政府的辦公大樓、行政院等,並因訊速被保安、警察抬走而結束行動。而在3月17日當天,本來是由一些溫和的公民團體在立法院旁舉辦集會,抗議服貿簽訂,然而當日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還是強行通過了服貿協議。公民團體本以為無功而返,然而激進的團體、學生卻突然衝進立法院議場,才開啟了後續的一連串抗爭。
太陽花學運,本質上是由一連串激進的社會運動者所引爆的抗爭行動,先由這些人使用違法的占領行動,方才產生後續一系列和平的上街示威。這個激進的占領行動起初,是接近「無大台」式的,在其後才自行組織出各種「部門」如媒體、現場秩序等,公民團體是「後續跟進」並一直甚少擔任領袖、決策角色的,許多均在學生領袖背後協助出謀劃策而已。
而本次的「青鳥行動」卻恰恰相反,在5月17日當晚,有十數位公民運動者到立法院側門舉牌抗議,其後聚集越來越多抗議者,高峰時接近千位。翻查臉書等紀錄,隨後是由「台灣經濟民主連合」(經民連)首先在18日開始呼籲群眾在21日在青島東路集會抗議,隨後21日、24日、28日的集會均由經民連及其他公民團體主辦,同時經民連依然扮演著主導集會論述的角色。與318當晚不同,517當晚的抗議者沒有主導論述,也無激進行動,青鳥行動的「主角」是主辦的四十個公民團體本身,而非激進的抗議者。青鳥行動並非由激進行動所引發的道德感召而動員的社會抗爭,而是公民團體透過理性論述、宣傳所動員產生的社會運動。
台灣上一次「激進」的「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已是十年前的太陽花,這十年間習慣和平上街的台灣人,也似乎對激進的策略無感,筆者在網路上、現場也甚少聽到有關占領與否的辯論,現場參與的群眾也似乎沒有占領議場的準備。立法院日前已三讀「國會改革法案」,表面上看起來這四日的上街似乎是以徒勞和以「失敗」告終,但正如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預示了2019年的反送中,經歷這十年和平抗爭的台灣人也多少需要演練社會運動這一「公民的技藝」。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