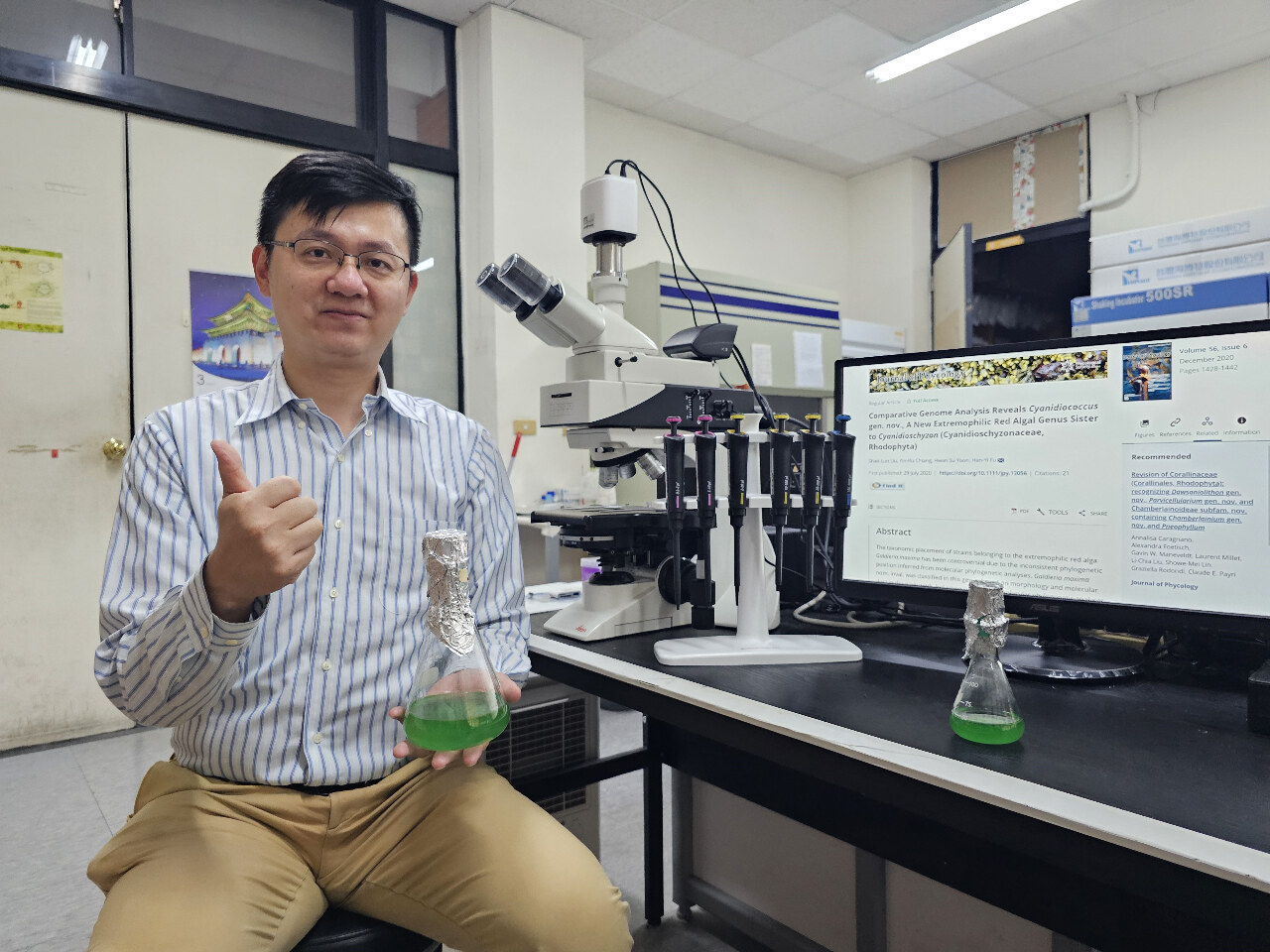經過上半年的居家隔離,上學聽課、與同學一起玩耍,已經成為了不少學生的心願。但對於不少殘障學生而言,由於出行無障礙、信息無障礙都未得到普及,再加上學校無法提供合理便利,那麼入學得到教育,則變成一件困難的事情。
即使順利入學,殘障學生卻有可能因為同學的偏見,隨後遭遇校園欺淩。而且,中國的家長與老師普遍缺乏殘障意識,可能無法介入為個體提供幫助與支持。這無疑加重了殘障學生在上學時遇到的困境,難以真正實現個體的受教育權。
在本文中,筆者採訪到一位經歷了校園欺淩的倖存者。在暴力下成長的他,曾不敢向老師與家長求助;但如今,他成為了一個反欺淩的社工,開始服務其他因殘障被霸淩的學生,為他們尋找一條預防暴力、與創傷和解的出路。
因殘障被惡意對待的個體,還有很多
經過長達一年的心理諮詢,曾宇慢慢從過往的陰影中復原,開始回歸正常的生活。
但在逐漸卸下壓力的同時,曾宇覺得自己有必要為殘障學生做一些事情,比如勸他們勇敢地求助,又或者是提醒家長與老師可以多點關心他們。於是,在大學畢業後,曾宇入職了一個公益機構,成為負責反對殘障欺淩項目的社工。
進入機構後,曾宇開始系統地學習與暴力相關的法律條例,以及如何預防暴力的有效措施。在此過程中,他接到一個聽障男生的求助,由於殘障經常被班上一個男生暴力對待,導致精神狀況堪憂,甚至不敢上學。
於是,曾宇開始詢問聽障男生的個人信息,與同事一起評估,如何為他提供一些幫助。這個聽障男孩與年少的曾宇一樣,由於障礙很少會主動表達,在原生家庭中缺乏家人的關心,在校園裏又得不到老師與同學的關注,就像是一個活生生的「隱形人」。
因此,當班上一個新來的插班生B,發現聽障男生在班上被排擠的狀態,便常常模擬電視劇中「黑社會」的姿態,不僅用言語羞辱他為「啞巴」,而且旁若無人地在校園內以暴力對待。
聽到男生反映的問題後,曾宇來到那所高中,準備與B面談。但意料之外的是,曾宇剛好就看到了B打聽障男生的現場。當時,B正坐在商店門外抽煙,看到聽障男生買完東西走出來,便起身一邊用腳踢男生,一邊迅速奪走他手上的零食。
當下,曾宇連忙走上前,先扶起被踢倒在地的男生,再大聲呵斥B的行為,質問他是否知道暴力行徑產生的惡劣影響。但B沒有理會曾宇,只是不斷地揮舞著拳頭,威脅聽障男生「明天放學等著」。雙方僵持了一會兒,B才扭頭離開。
看到霸淩發生後,曾宇與同事想好了一個干預方案。只要機構同事與志願者有空,他們都會陪同聽障男生一起放學,避免欺淩的情況發生。與此同時,他們還準備在同行的過程中,給聽障男生分享殘障賦權的信息,觀察他的心理健康狀況。
「除了分享我的經歷,我還需重塑他對殘障的認知,直至說服他變得勇敢一些。畢竟發生校園霸淩,如果不主動向老師、家長求助,反而縱容了更嚴重的暴力。」曾宇坦言,自己曾受惠於學姐的照顧,現在則是把同伴支持傳遞給年輕一代。
慢慢地,B看到男生長期有人陪伴,忌憚被志願者向老師投訴,便逐漸減少了騷擾。男生也在了解如何與同學、老師溝通自己的需要,以及自我保護後,開始在校園內有了安全感,轉而嘗試一個人回家。
偶爾,在男生不需要上課時,曾宇還會帶他去參加一些殘障活動,讓他在社群內部有一個傾訴空間,與解疑答惑的渠道。最後等到他畢業,曾宇還為男生申請了免費的心理諮詢,確保其心理健康狀況已經好轉,這才完成一次個案援助。
但在整個援助過程中,從接到求助到評估如何介入,再根據當事人狀況去調整干預方案,曾宇感慨仍然是「道阻且長」。即使《殘疾人教育條例》在2017年經過修訂,強調了保障教育平權,可殘障學生在校園內難以得到更多支持。
由此,曾宇開始思考,除了個案的援助,還需要從學校與原生家庭中入手,進行從社會結構上的反霸淩干預。
殘障教育平權的落地,缺乏社會支持
2018年,在當地殘聯的支持下,曾宇工作的NGO開始與學校、教育局合作,展開在校園內反對殘障霸淩的工作。
不過,在進行此項工作之前,曾宇與同事曾幾次向殘聯與教育局寫建議信,直至半年後才有反饋。他坦言,落實障礙者的教育平權,只是因為當地政府部門希望呈現好的「政績」,因此才願意表示提供資源聯結的支持。
但能夠從公權力中得到「允許」,無疑是隨後工作順利進行的前提。很快,在教育局的介紹與建議下,曾宇與同事來到了一個殘障學生比較多的高中,開始了以殘障平等為主題、定時定點的分享會,覆蓋從老師、學生到家長等受眾群體。
在分享會的第一場,曾宇先邀請了一些非殘障和殘障的家長,坐在一個大教室中,一起看一部殘障議題的電影。等觀影結束後,他再根據劇情,以及殘障孩子在校園遇到的真實困境,與兩方家長討論如何介入、溝通與解決的措施。
比如,對於一些本身對殘障有偏見的殘障家長,曾宇會提醒他們多關心自己的小孩,尊重他們的選擇與想法,不要因殘就貶低其個人價值或者過多干涉。又比如,如果非殘障家長知道自己孩子有殘障同學,同樣需要引導孩子學會平等與尊重的相處方式,避免同伴霸淩。
做完家長的分享會,曾宇接下來面對的受眾,便是殘障與非殘障的學生。在這個環節中,曾宇特意設置了一些與障礙有關的互動遊戲,比如閉著眼睛摸東西,或者是坐在輪椅上試著前行,讓學生們重新定義個體的障礙與環境無障礙的關係,從而開始共情彼此與互相支持。
最後,曾宇還會跟學校的老師、校長開一場討論會,分享如何在校園從源頭預防殘障欺淩的建議。比如在學校的圖書館中,可以增加一些殘障的書籍與繪本,讓學生可以外借;老師除了多關注殘障學生的心理健康,還可以多設置一些與障礙有關的課程,進而推進融合教育的落地。
雖然,這三場活動結束後,一些非殘障家長不以為然,覺得殘障與自己無關,便不願意採納曾宇提供的建議;但一些老師卻反饋,希望了解融合教育的信心。因此,這個活動後來持續了半年,主題從反暴力則延伸到殘障者的未來發展。
在採訪的最後,我問曾宇如何看待教育平權在中國的變化。畢竟,與他當初讀書相比,當時僅靠同伴支持,到如今已經成為了社工幫助他人,社會支持是否比過往更多。可曾宇當下先是點頭,隨後又沉默一會兒,嘆了一口氣。
曾宇坦言,或許從公權力的角度,中國對殘障者在教育平權上的條例進行了修訂,再加上民間有一直關注此議題的個體與NGO,已是一種進步。若殘障學生在校園受到霸淩,可以向當地殘聯或NGO諮詢與求助,再與校方對話要求進行干預。
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言論空間正在緊縮,殘障賦能的活動難以推廣,無疑導致了呼籲殘障教育平權的失聲。截至目前,據曾宇了解,仍關注此議題的現存NGO,僅僅是在新疆、北京與廣東三個地方,還未能在全國普遍落地。
「我們在反暴力議題的培訓,都是由香港或者臺灣的老師在引導。這就說明我們本土社群,還沒有積累太多的應對經驗。在沒有社會支持下,我們就如同一盤散沙般,只能在霸淩事件發生後,盡力去做一些如倡導等補救措施。」
事實上,曾宇的無奈,正是殘障議題在中國青黃不接的窘況——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裏,一扇門關閉了,一扇窗開著,有人已經看到窗外的「世外桃源」,卻只能繼續困在房中,努力打破束縛逃出去。
又或者說,明明從個體到社會結構,都已經看到房間裏的大象,最後選擇了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避而不談。可這些殘障學生在暴力陰影下,承受著眾多創傷,何時才能舒緩與和解呢?
延伸閱讀
在霸淩下成長的殘障學生:創傷與我,如影隨形(上)
集體缺乏無障礙意識讓中國社會殘障者成了隱形邊緣人
中國殘障媽媽育兒困境:被歧視又缺醫療環境 連家長日都不敢去
作者:林溢智 一位長期關注性別議題與障礙者權利的中國社工,透過報導與個人書寫,帶領讀者了解障礙者在中國社會的生存現狀。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