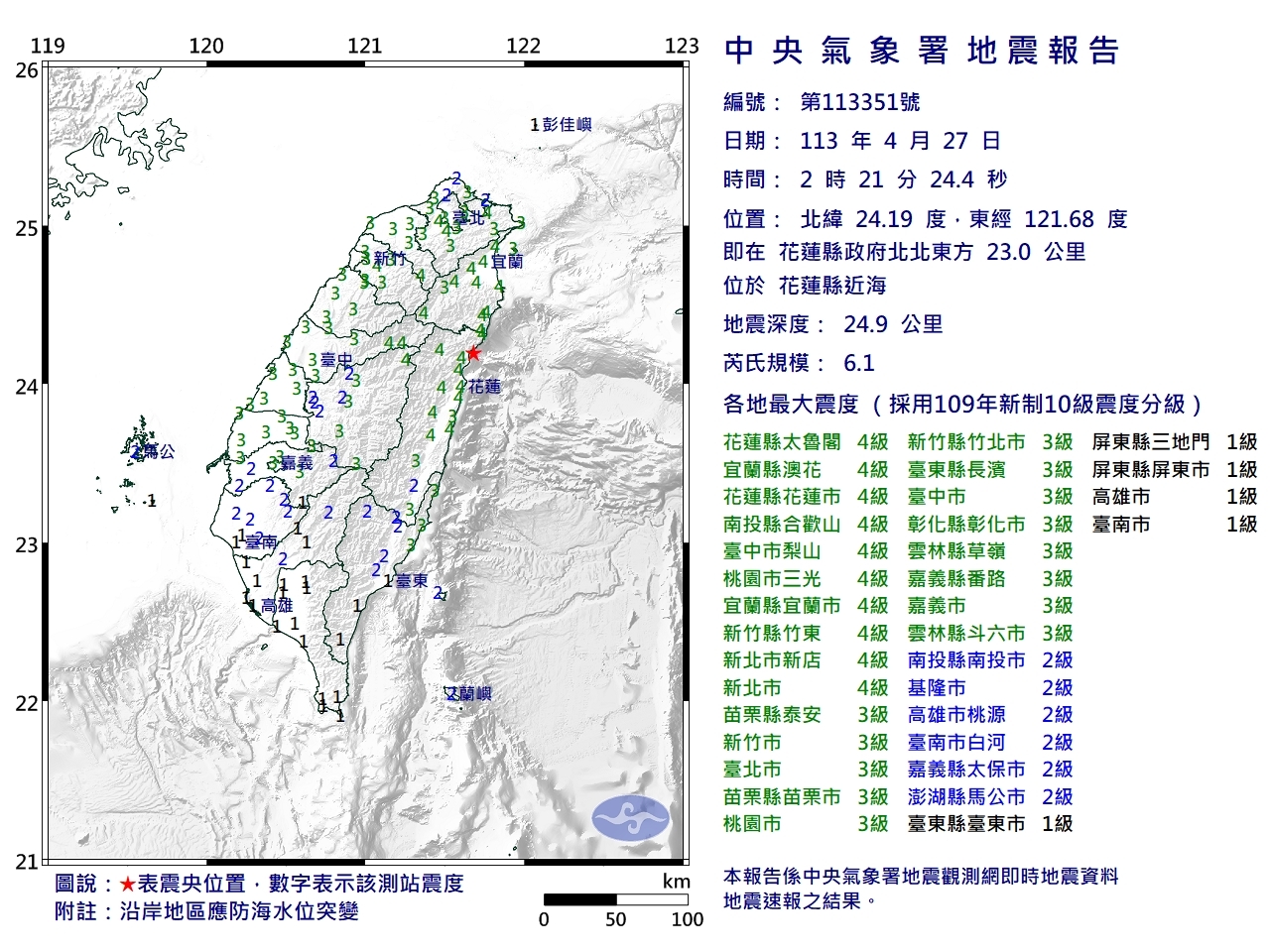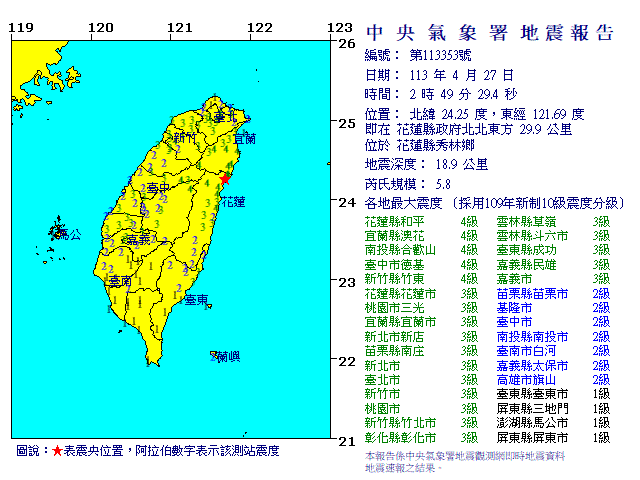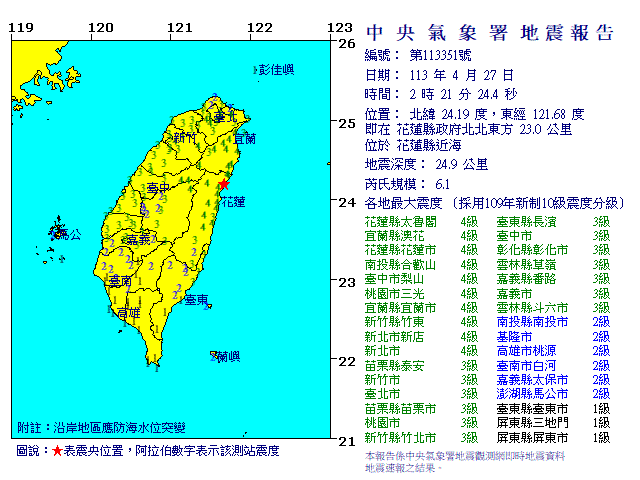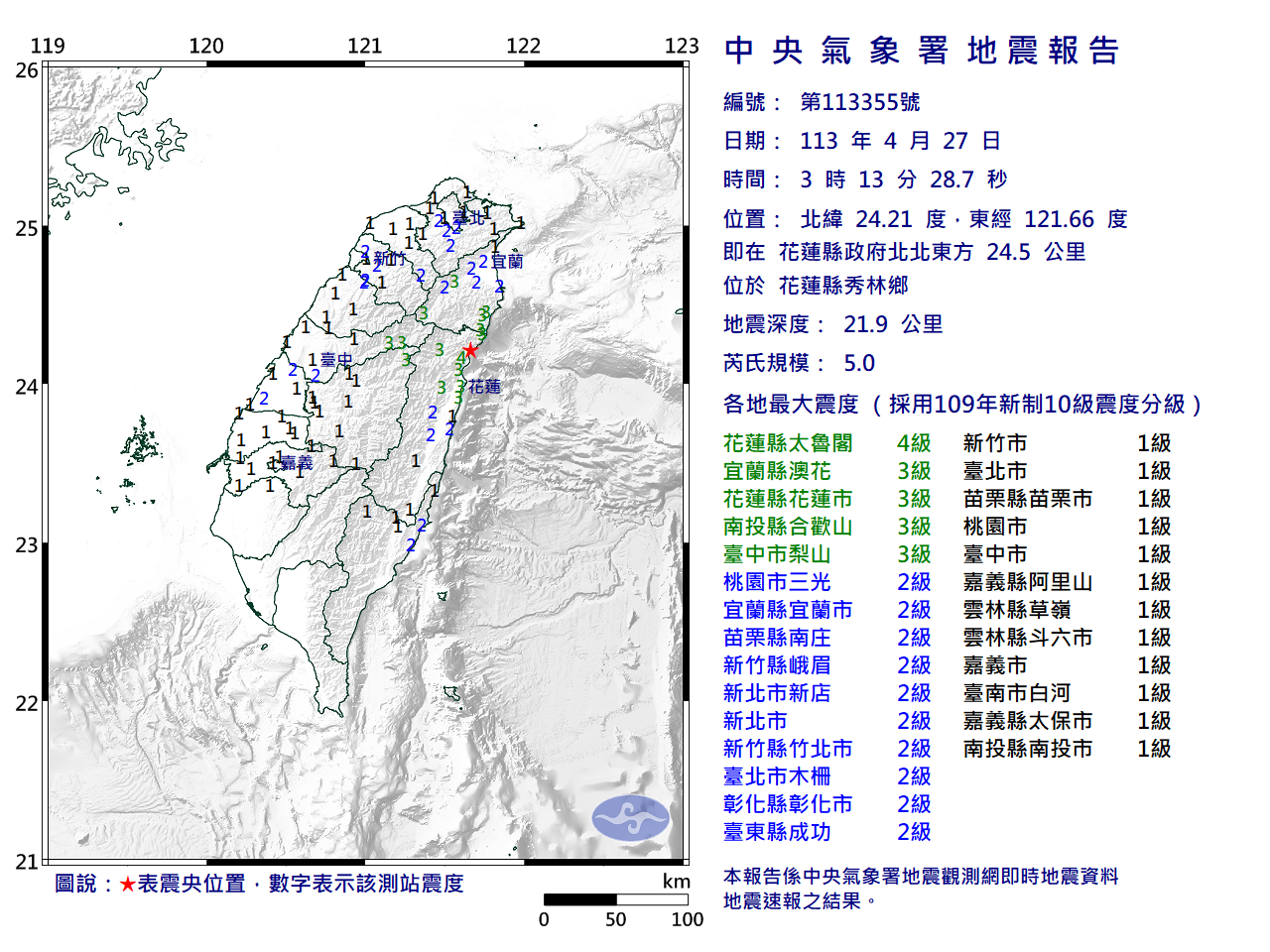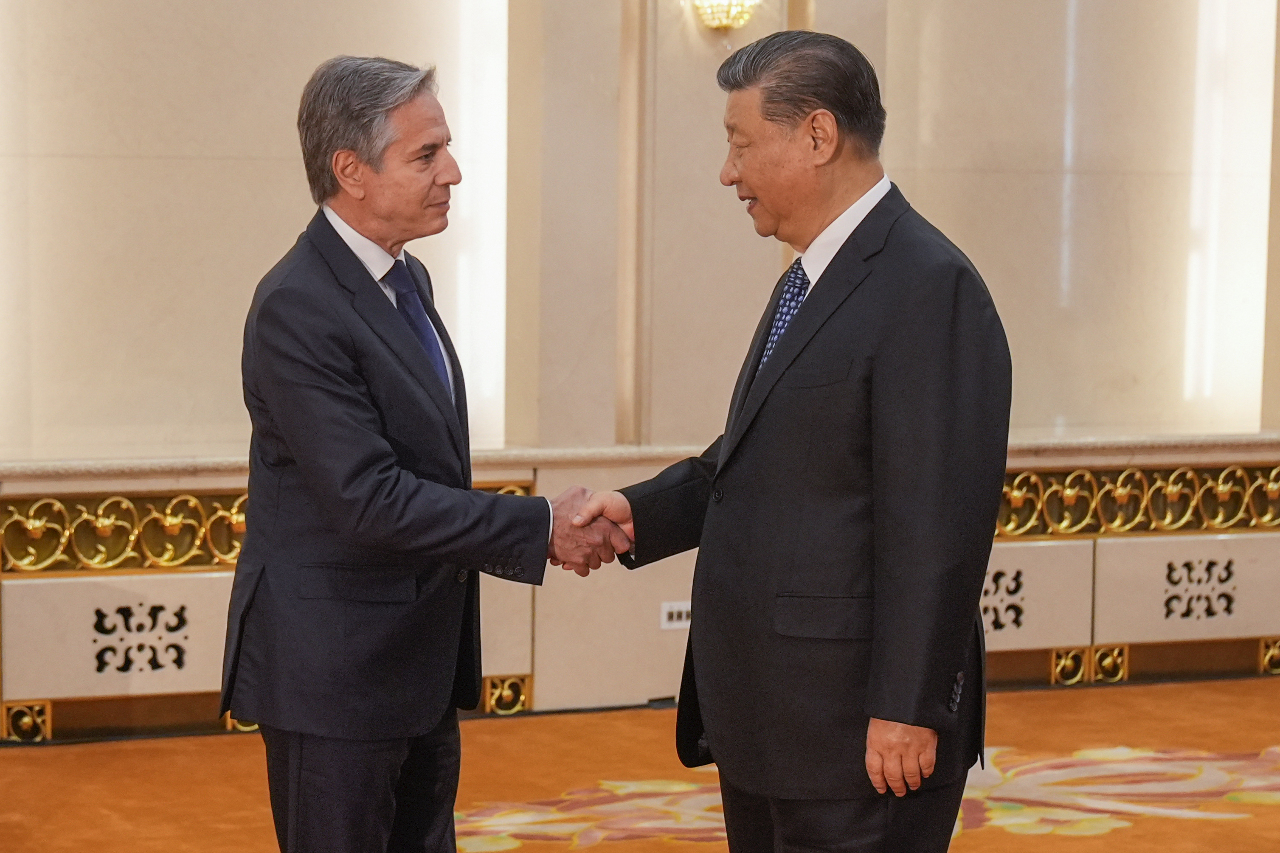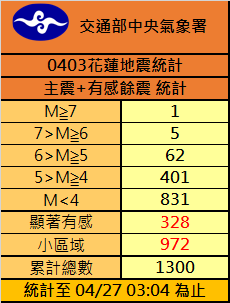母親的暴力管教,促成藝術家反叛的個性
向莉:翁冰女士,請講講你性格的形成。
翁冰: 1971 年我出生在中國無錫的一個小村莊。無錫是魚米之鄉,到處種著水稻,門口就是小河。我媽非常寶貝我姐和老二,尤其老二是兒子。懷上我後,媽媽身體不好,醫生不讓流產,不得不生下了我,於是她就把一切的不好全記到我頭上,情緒不好時,就打我。母親還經常當著別人面訓斥我,完全不顧及我的自尊心,我慢慢變得內向了。母親的不公正和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心理傷害非常大,但我從小就有反抗精神。老二經常欺負我,有一次老二又跟我發生爭執,我打不過就跑,他追到門口的小河,沒想到那裡有個斜坡,我一下就衝到河裡了,然後母親就把我從河裡拽出來,使勁打。我姐跑過來拉架,讓母親上工去,然後幫我洗臉讓我去睡覺,那時我已經折騰的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一次我聽見母親在生產隊的養蠶室跟人抱怨說,「她這麼一點大,就會用自殺來嚇唬我,上次就往河裡跳,把我也差點拖到河中間。將來結了婚,肯定一碰就要用自殺去嚇唬她老公的。」母親的這些話對我打擊非常非常大,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抑鬱的,那年我才9歲。一次我媽去上工了,老二打我,還威脅我說:「我要告訴媽媽,讓她回來再打你一頓」。於是,我就把辮子紮好,找了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穿上,蹲在上次差點淹死的那個地方,我想我媽回來要是打我,我就在這裡自殺,那是我第一次有自殺的念頭。
向莉:你如何走上藝術道路,成為一名畫家的?
翁冰:我從小就喜歡畫畫,有點天賦。我還沒讀書的時候,就拿著姐姐的童話書看,照著畫。那時候我沒有白紙和鉛筆,就拿一種白色的石子在牆上畫畫。上學之後,我就更喜歡畫畫了,但我媽認為畫畫會影響讀書,看到我畫畫,就會打我。讀高三的時候,母親正好不在家裡,我就買一些素描畫冊,照著臨摹,我可以畫得一模一樣。我舅舅看到了,他就找了無錫市少年宮的莊老師當我的繪畫老師,那時候離美術高考還有半年時間。於是,我每個禮拜天騎自行車一個多小時去找莊老師指點。三個月的時間,我就從畫石膏像到了畫真人肖像,進步非常快,每一幅畫都有進步。莊老師對我非常滿意,他說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有悟性的學生。上了三個月的素描課、三個月的水粉課,然後我就考上了南京師範大學,考試成績相當好,是當年無錫美術專業分數最高的一個。
翁冰:1991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一個中學做老師。因為我喜歡畫肖像,所以好多老師願意給我做模特,讓我畫肖像。但校長覺得我擾亂秩序,不讓我畫,還讓我去教歷史課。我說,「這不是我的專業,我教不好。」但還是被迫安排一半的時間去教歷史課,我覺得這個不是我要的。後來我懷孕了,有一陣妊娠反應非常大,醫生給開了十幾天的假。之後我發現,學校把我的工資都扣了,連替我交假條的老師都受到處分,我覺得很不公平。大概在那個高中教了一年書,我就辭職去了上海。因為沒有上海戶口,我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1995年我去了友邦保險公司,這是一家美國公司,不需要上海戶口,沒有底薪,全靠業績提成,結果我做得很好。由於忙於生計,沒時間畫畫,其間我只畫過一張水彩畫,畫我女兒的洋娃娃。在上海,我們住在一個12.8平方米的小房間,生活非常艱苦。因為沒有戶口,孩子上學還要繳納借讀費,所以必須努力賺錢。1997年我成立了一個公司,給房地產公司做雕塑、浮雕、噴泉一類的東西,賺了一些錢。2002年我就開始做職業藝術家,一直到現在。
個人覺醒,離開中國
向莉:請講講你觀念上的轉變。
翁冰:我母親的做法跟共產黨的做法是一致的,她對我實施獨裁,用暴力來「統治」我,我不能為自己辯解,否則就會挨打。我覺得不屬於這個家庭,我的性格、思想方面跟這個家庭差得太遠。所以從小我就想離開這個家,想要獲得自由。只有考上大學,我才能離開這個家,所以我讀書比較認真,這是我的一個奮鬥目標。由於從小在共產黨洗腦教育方式下長大,我們都以為共產黨有多麼了不起、共產黨有多麼好,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國民黨不好、很不爭氣、只能敗退到臺灣去。2000年有一次我丈夫對我說,抗日戰爭不是共產黨打贏的,其實抗日戰爭的主力是國民黨,共產黨基本是在搗亂,後來發生內戰,共產黨才奪了天下。我當時就跟他急了:「這怎麼可能?從小歷史書就麼寫的,難道都騙我們的嗎?」他一臉「秀才碰上兵,有理也說不清」的表情,把一肚子話憋回去了。後來我們就很少談這些話題。2002年我開始做職業畫家,就有時間看書了,我去圖書館辦了借書卡,還經常去福州路那邊買書。那個時候還有一些書沒有被禁掉,在圖書館也能看到一些歷史類的書,所以我也看到一些真實的東西。後來又看到楊顯惠寫的《定西孤兒院紀事》、《夾邊溝》一類的書,我就慢慢意識到「原來中國是這麼回事兒」,這只是一個粗淺的認識。我當時還覺得胡溫時代比以前好,經濟開始發展,日子過得蠻好,有一種還不錯的感覺。我丈夫的哥哥因為在國內經歷不公,去了日本,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我就跟他說,現在中國不錯,你們可以回來了,沒有必要一直在日本。我以前是不上網的,不喜歡電腦。一次在上海藝術博覽會上展出作品的時候,碰到女作家張惠玲,她建議我註冊一個微博。她說微博上什麼都有,政府不報導的,上面都有,並且往往是第一時間就有報導了。於是我就註冊了微博,上了微博之後,我發現,原來美好的外衣掀開來,裡邊是這個樣子的,有這麼多不公平的地方,在中國根本就是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第二個事情是就是「709大抓捕」,對我刺激很大,覺得政治迫害越來越嚴重。到了2016年,發生「吳良述律師的褲子被撕破」的事情,這個事件給我的震動蠻大的。我當時想要得到吳律師的那張照片,因為網路上的那張照片圖元(像素)很小。我跟於建嶸聯繫,問他有沒有圖元(像素)大一點的照片?他說,他沒有。所以我就沒畫成那張畫。不過,幸虧沒畫。如果畫了,我可能就沒有(在美國的)今天了。

翁冰《幻覺》油畫,2020年
翁冰:我覺得習近平上臺後,獨裁越發嚴重,這個國家也就越來越不好了。第三個事情是萬科的老闆王石被迫把萬科公司交給政府。我覺得資本家又要挨整了,以前剛解放的時候,中共也用相同的手法對付資本家,如今又要捲土重來了。這些事情讓我覺得國內越來越不自由了,就鼓勵女兒出國。我女兒雖說因為我們一直會跟她講六四什麼的,知道一些真相,比一般的孩子懂得多,但她不願意離開這個生她養她的地方。她也沒經歷過腥風血雨,所以她更想待在中國,想在清華或者在復旦有一個教職。2014年我們帶女兒到美國旅遊,去了普林斯頓、康奈爾等很多大學,之後她的感受就不一樣了。女兒讀清華,大三暑假有一個去哈佛學習交流的機會,那個項目由哈佛大學提供一年的學費,清華大學提供一年的生活費。哈佛大學同意讓我女兒來美國學習,清華大學不讓她出來。我們就說自己出生活費,但清華還是設立了很多別的卡,不想讓她出來。我女兒蠻堅強的,一步一步爭取到出國的機會。女兒在跟清華做鬥爭的時候,感覺到這個體制的可怕,這也是促使她後來決定來美國留學的一個主要原因。她的畢業論文,哈佛的導師給她97分。她從哈佛回去後,清華竟然把分數改成91分。難道就因為我女兒沒有聽他們的話,去美國上學了,他們就利用權利,把我女兒的分數改到班裡最差?但是改了也沒有用,因為分數就在哈佛那裡,沒有影響她被DUKE大學錄取。從這一系列的事情裡面,我女兒徹底看清了,在中國不是憑真本事,完全是權力說了算,所以後來她就義無反顧來美國留學了。中國政府在網路上的禁言、言論審查、迫害一些說真話的人、員警可以在路上隨便抓人,人們沒有人身安全,這讓我非常恐懼。另外,老百姓之間相互不談政治,每當我一涉及這個話題,他們就會說:「我們國家現在很好,你想的太多了」,避開這些話題,就像鴕鳥一樣。這也讓我看到他們內心的恐懼,我覺得這非常可怕。我想,這個國家我們不能再待,我要離開這裡。

翁冰《六四真相》:90x130,油畫,2020年
作品被撤出展廳,在美國成功維權
向莉:你們為什麼選擇來美國?
翁冰:因為我覺得美國包容性強,比較民主、開放和自由,我女兒也正好到美國讀博士。我們一開始是想申請傑出人才移民,找了律師準備材料。2018年10月我們來美國是為了籌備畫展,因為我在2019年1月和12月在北卡的Cary City有兩個展覽,已經簽好了協議。
向莉:你從在什麼時候開始構思《沼澤地》那些畫的?
翁冰:在到美國之前,我在國內看到微博封號、員警抓人這一類的事情越來越多,長時間生活在恐懼當中,經常失眠。在失眠的過程當中,我腦子裡就在構思那些畫,包括習近平站在毛澤東肩膀上,毛澤東淹沒在骷髏裡邊的那幅畫,在我腦子裡縈繞了很久。2018年7月的董瑤瓊潑墨事件對我的刺激很大。我想她只是房地產仲介公司的一個普通女孩,做了這件事情,哪怕是做錯了,政府也不應該把她送進精神病院,這麼迫害她!這事情出來後,舉國上下的人都很自覺去幫共產黨指責那個女孩,這就是全民網暴。我覺得共產黨一手遮天,擁有軍隊、媒體,老百姓啥辦法也沒有。防火牆隔絕了之後,聽不到外面的聲音,老百姓還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覺得歲月靜好。潑墨女出事兩個月後,這幾幅畫已經在我腦子裡完成了,但我一直沒敢畫,因為怕畫出來,我們回不了國或者會連累到我女兒。我跟我女兒說,這個國家實在不像樣子了,我怕我哪天回去就出不來了,害怕會和你分開,就像王母娘娘用簪子一劃,我們就一輩子見不了面。我問女兒,我想畫這些畫,但是畫了,可能我們再也回不去了,你支持我畫嗎?我女兒那個時候已經病得很重了。她說:「那就畫吧,我最多不回去罷了。」然後,我就趕緊畫,一個月的時間,我畫了這三幅畫。以我的體力,以前一個月最多能画一幅畫。那時候我焦慮症很嚴重,還得了痔瘡、肛裂,疼得我都坐不下,但還是拼命把三幅畫趕出來了。

翁冰《沼澤地》 油畫 96x144cm 2018年12月

翁冰《一手遮天》油畫 43x48cm 2019年1月

翁冰《罪證》 54x70cm 油畫 2019年1月
向莉:你作品被撤掉的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翁冰:2019年1月18日下午我去Cary City Center布展,展覽的名字是「生命的綻放」。當時那裡的負責人看到這些畫非常高興,覺得我畫得很好,還說我很有正義感,為我感到驕傲。之前我也問過一些朋友,這些畫展出的話,會怎麼樣?他們說,沒問題,美國是言論自由的國家,不會把你的畫怎麼樣的。我想,Cary City是個北卡的小城市,中共未必會曉得我這個展覽。沒想到在1月23日,我就接到主辦方的郵件,讓我移除這《沼澤地》、《一手遮天》、《罪證》這三幅畫。我覺得很奇怪,我說:「布展那天你們不是說這幾幅畫很好嗎?美國不是有言論自由嗎?」對方說,有人反映這幾幅畫不好。我說:「每一件作品出來肯定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不能因為有人不喜歡,就讓我把它下架。」對方又說,作品裡不能有政治。我說,簽約時你們又沒告訴我不能有政治。然後他說,一定要下架。我說,我肯定不會下架的,假如你們利用權力硬把它拿走,就是濫用職權。1月25日reception的時候,我去看,那三幅畫都被他們從牆上移除,堆在走廊裡。我很惱火,就找來一個幫助reception的工作人員,把那三幅畫拿出來,因為沒有梯子,畫沒法掛在牆上,我就把它們放在畫架上展出。
翁冰:我把這件事公佈在Facebook上了,還找了周鋒鎖他們。周鋒鎖說,那些畫很震撼,沒想到居然被下架了。你註冊一個Twitter,把這件事發到Twitter上。於是,我發了推文,周鋒鎖就把這個事情轉發出來了,沒幾天閱讀量就達到三四萬了。之後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了我。後來有一個非盈利組織「全國反審查聯盟」來找我核實我的油畫遭到審查和下架的事情。這個機構的藝術項目助理喬伊•加內特專門和我進行聯繫,她還介紹了北卡的一個電視臺ABC11-WTVD的記者Michael Perchick介入採訪。全國反審查聯盟也去找了Cary city市政府,讓他們必須把畫掛回去,否則涉嫌違法,他們會去現場監督。主辦方覺得很尷尬,他們不得不當著記者面,把那三幅畫掛回到原來的地方,但他們並沒有正式向我道歉。作為一種補償,主辦方把我的畫展延期了兩個星期。有好些人跟我說,那些畫終於又回到牆上,他們很高興,認為我是值得尊敬的。後來,我大概知道贊助政府舉辦展覽的是誰了,也就是說辦活動的贊助經費有一部分來自中國。Cary City Center的人問我,這邊有沒有孔子學院?我說,有。對方說,很有可能就是孔子學院的人幹的。當然,這些都只是猜測。本來我們已經買好4月的機票,準備回國給我先生陳優鋼做心臟手術。因為這件事情鬧大了,我們就沒敢回國,也來不及等傑出人才移民,最後選擇了申請政治庇護,選擇了流亡美國。12月我的另一個展覽如期舉行,但主辦方沒有通過我第二年的展覽申請。

翁冰《花叢中》 21x30 油畫 2023年

翁冰《遐想》 28x23 油畫 2019年
新移民,任重道遠
向莉:這個事情改變了你的生活。你們在美國的生活跟在中國有什麼不一樣?
翁冰:是的,我們不能回國了。我覺得改變最大的是語言和生活習慣。語言是人類表達的主要途徑,在美國不會說英語就像個啞巴。比如畫展糾紛,假如我是一個美國人,他們就不敢這麼做。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英語不好,你的權利不能100%的像美國人一樣的去獲得和運用。另外,你也很難賺錢。比如說,我本來可以靠帶學生畫畫,生活得很好,但由於語言不通,在這兒我就很難教學生,跟美國畫廊交流也成了一個問題。不懂英語、不瞭解美國的風俗習慣,是一個很大的生活障礙。對於我們這樣年齡的人,突然不能回國,生活壓力是相當大的。我女兒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她不敢讓同學知道這件事情,否則就有人不願意跟她做朋友。當時,我女兒已經病了,得了威爾遜病。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疾病,是由基因造成的,但會以心理問題的方式呈現。她本身就很焦慮,工作壓力又很大,我們這件事情又給她很大的壓力,讓她更焦慮,對她的病情是有一定推動作用的。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她就搬出去,不跟我們住一塊了,在經濟上也造成了一定壓力。
翁冰:我女兒2021年5月被確診得了威爾遜病,7月她到斯坦福大學做博士後。2022年3月底她再次發病,醫生診斷說,在24-48小時內她必須要做肝移植,否則人就不行了。當時我想,這麼短的時間內怎麼可能會有肝呢?所以我跟醫生說,可以移植我的肝。他說:「不行。因為僅僅檢測你的肝是否和你女兒匹配這一點,就需要四、五天時間,那個時候你女兒早就不在了。只有靠捐獻者,我們有一個完善的一個捐獻系統。」他說:「你不用擔心,這都是看緊急程度評分的。你女兒生病的緊急程度現在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最頂級,她排在肝源等待清單的第一個。只要有跟她相匹配的肝源,肯定移植給她。」但他們也沒辦法知道那個肝到底會是什麼時候到,因為這種東西就是人家發生意外事故,才會有緊急肝源,這要看運氣的。後來大概等了二十幾個小時,就有肝捐獻者去世,可供移植的肝到了。病房裡有兩個護士輪流照顧我女兒,最危急的時候,那個該下班的護士不下班,一直陪著我女兒,兩個護士一起陪著,直到半夜裡才回去。第二天,另一個護士也不回去,她說很怕我女兒不行了,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走掉。在中國只有那些高幹才有特供肝源,才會在二十幾個小時之內得到肝源,老百姓是拿不到的。正因為美國社會透明,所以願意捐獻器官的人就多。在美國,我們去考駕照就會被問到,你願意捐獻器官嗎?大部分人都說願意,所以器官捐獻的來源就多。另外斯坦福醫院的技術是世界一流的,他們在移植方面成功率非常高。像我女兒病到這個程度,風險非常大,而斯坦福醫院從技術上保證了手術的成功,最終救活了我女兒。
向莉:到美國之後,你觀念上有沒有變化?
翁冰:到美國後,我們對中國政府的性質越看越清楚了,覺得離開中國來美國,是對的。假如我們還在中國的話,早晚是不能忍受的。比如說三年疫情,我們這種性格是不可能被關在家裡那麼久的;政府還把鐵門給焊死,我們肯定要反抗,結果很有可能就是我先生陳優鋼被抓進去。像我女兒得了這個病,要是在國內,她肯定死了。國內不可能在一天內給你普通老百姓一個肝源,不可能!所以幸虧她是在美國,作為一個平民,拿到一個肝。在美國,在斯坦福醫院,不會問你是誰、什麼種族、什麼年齡、什麼性別,也不會考慮你的家庭背景,只會考慮你是一個人、一個生命,他們現在要挽救你的生命,這是他們唯一要考慮的。她的病情最緊急,她的肝移植需求排在最優先的位置,他們就把那個肝移植給我女兒了。
翁冰:還有我根本沒想到畫展出了問題,會有那麼多美國人來幫我,會有那麼多媒體來採訪。那個全國反審查聯盟,我都不曉得還有這種機構存在,他們那麼負責地幫你解決問題,沒有向我要一分錢,事情結束後他們再也沒有跟我有過聯繫。不像在中國,做什麼都要靠關係。在美國,他們幫助我,完全就是因為正義感,這讓我非常感動。在發生問題後,可以找到解決的路徑,會有很多人來無償的幫助你,為你伸張正義。比如說Cary City Center的很多人,看到我的畫掛回去了,就很高興,說一些鼓勵的話。如果這事發生在中國,政府肯定會打壓藝術家,然後老百姓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這是本質上的一個區別。一開始我也很憤怒,覺得美國跟中國一樣。但通過這件事情,我發現其實中國的民眾基礎和美國的民眾基礎在兩個制度下是截然相反的。正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群眾基礎在,美國的民主才能存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使得政府部門想要做壞事,卻做不成。所以,我覺得民主體現在美國的方方面面,滲透在每一個老百姓的心裡。
向莉:在你的流亡生涯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翁冰:最讓我感動的還是人,美國人會盡力幫助你。因為女兒病了,我們英語又不好,日常生活當中碰到很多困難。我碰到一個在美國出生的華人勞先生,他會講一點中文,幫了我們不少忙。但凡我有什麼事情跟他說,他可以放下他家裡的事情來幫助我。比如,我們不知道怎麼看病,他就幫我們聯絡、介紹醫生。因為我們剛剛來,身份還沒確定,沒拿到工卡,也沒有買保險。因為畫展的事,我先生無法回中國做手術,於是他的心臟越來越不好。醫生就給他開了一個做彩超的單子,大概要花2000多美金。我們看不起,我說不做了。醫生馬上就說:「不要緊,你付個50塊都可以,你先去檢查,然後我們給你一張表格,你填了,有機構會給你豁免或者替你付帳單的。」我很不好意思,就付了100美金,然後填表格,最後看病的錢全豁免了,一分錢都沒要我們出,後來因為我是他妻子,我以後看病的錢也都豁免了。北卡和加州不太一樣,那邊沒有醫療白卡。印象最深的就是受到大家的無償幫助和醫院的免費治療。我女兒病了後,勞先生和我的兩個鄰居一直幫助照看我家和我家的貓咪。有一個鄰居特別讓我感動。我需要搬家,剩下的時間來不及打包家裡的東西,那個鄰居竟然不顧我當時得了新冠,他戴著口罩,把工作放在一邊,來幫我打包。美國人真的非常真誠和友善!

2010年上海,畫家翁冰和她的先生陳優鋼。
向莉:你想對未來的流亡者說什麼?
翁冰:我覺得語言是一個問題,假如語言問題解決了,會解決很多實際困難。千萬不要因為自己年紀大就放棄學習語言,要抓住一切機會去學習。其次,我們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確實會碰到很多困難,但哪怕遇到天塌的困難,都不要絕望和放棄。你可以在網路上或社區裡說出自己的困難,就會有人來幫你或者給你建議,最終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法。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