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籍移工在台人數逼近70萬大關,其中社福勞工已超過25萬人,他們是台灣高齡社會下長期照顧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但是,社會中曾發生女性家庭看護工遭雇主性侵,被害人錄下痛苦過程蒐證,因而引發軒然大波;雇主與移工是在權勢關係下被迫性交案件的典型,當她們鼓起勇氣血淚控訴後,得經歷多少關卡,才能將惡狼定罪?
等待與煎熬 庇護中心內心情複雜
記者問:『(原音)今天吃什麼啊?』
印尼移工Su(化名)說:『(原音)這個…印尼炒麵。』
記者問:『(原音)中午幾個人吃呢?』
印尼移工Su(化名)說:『(原音)有人出去找工作了了,今天6個人吃。』
一間外籍移工庇護中心裡,不到中午十二點,早已香氣四溢,負責掌廚的移工姐妹正在準備中餐,今天來點兒家鄉味-印尼炒麵;接著,走入她們的寢室,一層樓有2個大房間,每間各有十個床位,房內雖然不算寬敞,但是,總算有一個讓她們遮風避雨的空間。
在政府的保障下,曾是被害者的她們與一般移工不同,這時,也擁有了自由選擇雇主的權利。是的!就像一般台灣人一樣,面試上班去。
印尼移工Ani(化名),她說:『(原音)現在的工作是照顧一個帕金森氏症的阿嬤,要照顧她的日常生活和幫她洗澡;雇主人很好,大部份是中午過後再去上班,所以上午若要出去買東西,雇主也都允許我出去買東西,我一個月可以休假2天,只要先跟雇主協調,只是要先說,否則阿嬤没有人照料。』
Ani在工作媒合後,終於等到一個好的雇主,熬過5個月没有收入的日子後,一切都值得,但不是每個姐妹都能頂住没有錢寄回家的壓力。
菲律賓女孩Mary曾入住庇護中心2回,她說,當時一心只想快快找到新工作,怎知羊入虎口,遇到猥褻她的阿公,Mary說:『(原音)我當時没有選擇,因為我一定要快點工作賺錢,才能寄錢回家……。』
#Metoo女孩-菲律賓移工Mary受訪,指控「阿公」企圖拿錢與她性交易,在她拒絕後,「阿公」憤而凌虐她/詹婉如 攝
支持系統不足 監委:求助者得付出代價
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這份調查報告中,我自己覺得值得大家重視的地方是,受害者七成是來自家庭看護工,看護工和產業工不同的地方在哪裡?產業工在工廠,他一定有同儕朋友,住在宿舍相對安全;看護工則是一個人走進一個家庭,相對她勢單力薄。』
監察委員王美玉翻開今年5月提出的調查報告,她指著特別被圈起來的633數字說,這是2012年至今年2月為止,衛生福利部接獲外籍移工被性侵的通報案件量,其中70%為家庭看護工。
經過八個月的實地訪查,她相當清楚,一個移工女孩從鼓起勇氣通報、成案到最後的司法訴訟得花多少功夫。
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支援她的資源非常少,比如說通報後立即被帶離不良雇主家,她没有工作收入,來台灣的仲介貸款每天要繳利息,不僅没有薪水,回過頭家裡還需要錢,所以你想想看,被害者通報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遇到危險要求助,是人求生的本能,但對來台賺錢改善家計的女孩來說,得考量的更多!由於移工與雇主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中途中止契約困難等因素,使得移工在遭受性侵害時多數選擇「隱忍」或「逃逸」,但是,這都不是長久之計。
若最後決定尋求政府協助,但是,光打求助電話就是第一道關卡,勵馨基金會外勞庇護中心督導李凱莉就談到,曾協助過一名身處偏鄉,費盡千辛萬苦,才得以對外聯絡的女孩,她說:『(原音)外在的支持和資訊的給予會讓她們有勇氣打1955求助電話,我們也有看到一個姐妹工作在偏遠山區,電話也不通,所以她只有趁没有人在的時候偷偷跑到外面,趁有訊號的時候偷偷發一點簡訊,丟出一點訊息後,慢慢地才能由她的朋友協助通報。』
「Metoo女孩很多不敢講,也未受基本勞動法令的保障!」勵馨基金會社工督導李凱莉看見女孩受害中的結構性問題/詹婉如 攝
無人證物證 法庭正義難以取得
就算女孩在面對受害處境時,大聲求救,但講求證據的法庭上,真能給被害者一個公道嗎?經常承辦相關案件的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宋一心律師說,實務上,若雇主存心不讓移工使用手機,在没有目擊者、缺乏事發現場的錄音、錄影證物,事後又有没有驗傷舉證,案件很難成立,導致移工受害者經常成為法庭裡的弱勢。
宋一心律師說:『(原音)法庭中法官都會有無罪推定的認知,但對一個外勞而言,我不知道她究竟應該做到什麼程度?有一個案子是那個法官認為,妳曾經可以打電話求助,也有發簡訊,但是為何簡訊當中没有提到受侵害的事?但站在我們的立場是,我電話也打了,陌生人也求助了,為何我還要簡訊再求救一次?這個案子法官從很多矛盾的地方集結起來,所以認為被害者指控不能採信;一個台灣人如果真的在職場上發生性騷擾或侵害問題,我們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對外發聲,可是這對外籍移工來說,可能没有辦法。』
想到移工面臨的困境,義務協助的宋律師不禁大大倒抽了口氣;現實中,進入司法程序,每個環節都重要,制度上期待「完美被害人」,本國人不一定都能達到,更何況來自語言、文化思維迥異的移工?
看見困境 民間司法通譯協會成立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說:『(原音)當初當外事警察是覺得在處理外國人的事務還蠻新鮮的,在學校就覺得說可能跟其他性質的警察工作是不太一樣,所以有一點好奇,也有一點興趣。(記者問:所以你會講一點東南亞語囉?)會講他們的語言對他們來基本上就是一種尊重,語言可以把人拉近距離,其實我們學的還蠻簡單的,就問你叫什麼名字、住址是哪裡的啊?然後你來台灣做什麼啊?什麼時候來台灣啊?都是那些問筆錄的話,呵。』

陳允萍深感非本國人在台灣司法上語言弱勢,2014年創辦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圖 陳允萍提供)
陳允萍一名台灣外事警察,在台東負責在台外國人管理業務,1992年,台灣引入外籍移工的第一年,他從學校畢業;受訪時,陳警官笑著說,自己的南亞語程度,僅適用於問筆錄,但也就是親身經歷許多移工案件,深感移工在台灣司法上的弱勢,於是,他在2014年創辦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陳允萍說:『(原音)其實我們國家對司法通譯人員的能力、資格都未嚴格規範,以至只會要會雙語的一個人就可以去通譯,我覺得政府這件事情上很可惡,但是這個非常無奈,現在全國的各個機關,除了法院地檢署他們培訓的叫司法通譯之外,其他的都用通譯一句含糊帶過;這些叫通譯人員,比如說我們國家有3000個訓練過的通譯,他們大概占了兩千五百或兩千六百多個人,其他真正有到法院去做比較嚴格訓練的那些司法通譯人員,他們也不過占全部的1/5不到。』
陳允萍強調,通譯要具備司法專業與中立性,因為,進入訴訟程序後,通譯的良窳,幾乎就註定案件的成敗。
經常處理移工案件的宋一心律師,有感而發地說:『(原音)檢察官問她(移工)說,你承不承認跟人家通姦?她是這個案件的被告,通譯就譯成你有没有跟雇主發生性行為?那位外勞就說有,我有跟雇主發生性行為,通譯就翻到這裡,可是外勞還有說一句,我是被逼的!後面這句通譯就没有譯;那法官認為,妳就是通姦罪了,因為妳自己也承認了;關乎到被逼就很有趣,妳是怎麼被逼法?是涉及強制性交?還是被利用權勢性交?就不知道了,因為一切問到這裡就結束了。』
原本是性侵案件,因為通譯轉譯不完全,最後竟然被認定為兩情相悅,加害者無罪。
懷抱夢想,跨海異鄉,面對困境時,誰能拉一把?

無留下求助證明,法庭上,法官研判案件的確實性及嚴重性將產生困難/Forter示意圖
事前防範 查察工作落實不易
於是,政府設計了外勞查察員的角色,主動出擊!
盧敬明說:『(原音)(按門鈴聲)你好,我是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盧先生,今天主要是要來訪查您所申請的外勞,這是我的識別證。』
 外勞查察員盧敬明(左)和陳銘傑(右),穿著紅背心,穿梭於幅員遼闊的大台北地區,進行移工訪查工作。
外勞查察員盧敬明(左)和陳銘傑(右),穿著紅背心,穿梭於幅員遼闊的大台北地區,進行移工訪查工作。
盧敬明,一名具有12年年資的外勞查察員,穿著印有「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字樣的紅背心、騎著灰色機車,穿梭於幅員遼闊的大台北地區。
目前,新北市大約有三十多位像敬明一樣的查察員,每天訪視七個聘用移工的家庭。敬明說:『(原音)最主要會先問移工在這裡的主要工作是照顧誰,工作時間大約幾點到幾點,中間有没有休息時間,有没有領到薪資,是如何的給付方式?再來會詢問對外溝通管道是否暢通?你在這裡有没有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問題,都會提供有移工母語字樣的問卷讓移工勾選。』
但是,進入家戶執行公權力不是每次受歡迎,吃閉門羹是家常便飯,弱勢的移工朋友在雇主的監視下也不一定能暢所欲言,所以,敬明就曾遇過移工私下塞字條給他的情況。
敬明說:『(原音)嗯,有一個案例是移工知道我當天要過去,所以他有先寫好一張問題,當我要離去的時候,他偷偷塞給我;他可能是怕僱主知道,不敢現場反應,所以在我離開的時候塞字條給我,請求協助。』
拿到字條後,敬明立即帶回勞工局,在翻譯的協助下,解決移工不知能向誰傾訴的困境。
移工政策不周延 監院監督補人力
查察人員是家庭內移工女孩安全把關者,但並非每個縣市都有充足的執行人力,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就特別提及台灣外勞查察員的角色,當中描述,雖政府有相關預防機制,運作因檢查效能不足,仍無法防範於未然。
在這份調查報告提出後5個月,究竟政府相關單位如何回應?監察委員王美玉說:『(原音)這2年台灣的外籍移工大量攀升,勞動部也承認,隨著外籍移工人數大量增加,成長快廿萬人,你還用一樣的人力去做勞檢工作,當然是力不從心;所以我案子提出來後,勞動部已經在5月24日有一個檢討會議,會議當中決議增加76人,至少現在大約有350勞動檢察員,以彌補人力不足問題。』

監察委員王美玉認為,在移工政策上,政府應提出更周延且強而有力的支持政策/詹婉如 攝
官司打贏 移工:他會坐牢嗎?
相對保守的亞洲的文化裡,認為被性侵是羞恥、骯髒的,擔心別人看不起她,更不敢將事情告訴任何人,但是,這不但是妳的錯,妳的勇敢還會幫助其他姐妹不再受害。
然而,若贏了官司法院宣判後,姐妹們最關心的不是金錢的賠償,而是這個!
宋律師說:『(原音)官司打贏了,這個移工朋友是告訴我說,打贏了?那他有坐牢嗎?她只關心加害者有没有坐牢,其他金錢的補償,她並没有那麼在乎;另外一個移工也是,被告其實没有任何財產,她說没有關係,因為被告被判很多年,真的!她說没關係,因為加害者有得到應有懲罰,她就OK了。』
受害女孩Mary(化名)說:『(原音)我會跟妳說我的故事,是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了,我應該忘了過去的不愉快,繼續往下走。』
庇護中心一隅,專門收容遭逢不當對待的移工女性,也是Me too女孩安全避風港/詹婉如 攝
突破保守國情 #MeToo受害者的勇氣
#MeToo行動從2017年開始,成為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諸多影視明星、體育選手勇敢站出來,讉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這些慘痛的經歷,每分每秒地也發生在弱勢移工身上,李凱莉督導說:『(原音)台灣民眾可能不是冷漠的,而是說他不了解,然後會有很多的恐懼、擔心、害怕;可是我相信,不會有雇主到外面跟別人說,其實我每天就會對她摸一下,或者做了什麼事,不可能會有這些訊息出來,唯一的訊息來源是移工自己講,除非事情很嚴重,不然,以她們的民族性,頂多跟一、兩個至親好友講,不太可能會上Facebook大聲說,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因為即使是我們本國人發生事情,可能也不會希望大家都知道。MeToo是一個國際性的倡議,但是,它也更關乎就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個移工,她們的人身自由和身體自主權。』
集眾人之力 為異鄉者平權努力
 2018年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課程,培訓各語種專業司法通譯,為語言平權努力。(圖 陳允萍提供)
2018年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課程,培訓各語種專業司法通譯,為語言平權努力。(圖 陳允萍提供)
移工受限於語言,不易為自己發聲,但是,近年有不少台灣人為「失語」的他們站出來,讓外界看到台灣「為語言不通者的人權而努力」,陳允萍說:『(原音)我希望建立一個良善的司法通譯制度,讓他們在不幸陷入司法訴訟的過程當中,國家可以提供他一個非常有能力的通譯,讓他在整個過程當中沒有損失他的權益,我想這個就是我很希望去做而且需要做好的。』
然而,這些行動,正是台灣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將其國內法化後,應給予的最基本人權保障,無論他,來自何方。
【延伸閱讀】在台移工#MeToo(一)我們不是唯一
【延伸閱讀】在台移工#MeToo(三) 立法中的失語者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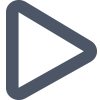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