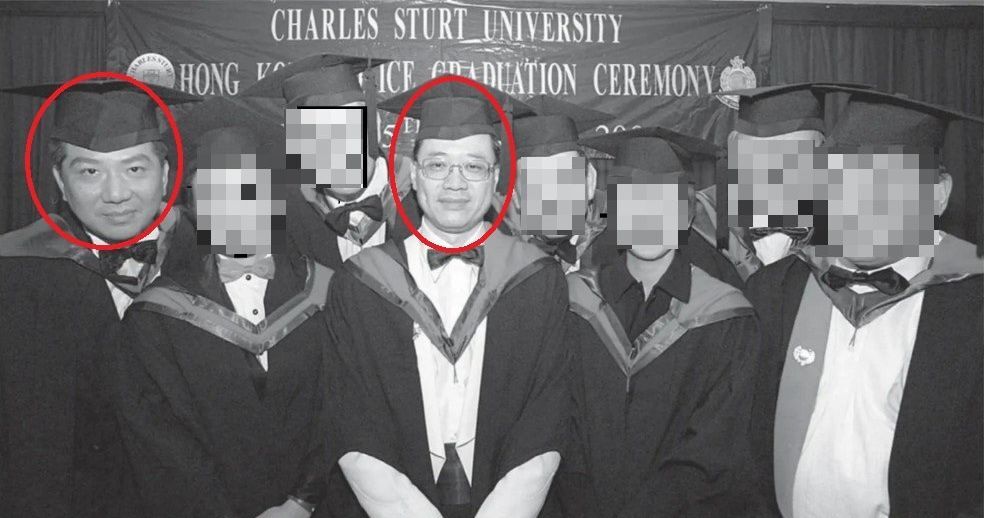自閉兒遭不當管教 暴露無處可去窘境

漢平爸爸一談到兒子在希伯倫遭到不當管教就怒氣難消(曾國華攝)
「(原音)真的是用水管打喔,各位那真的打下去,就像是巴掌這麼大,黑色的,當時那個醫生的形容說,就像是木炭的顏色一樣呀,各位可以想像,你的孩子有兩個木炭烙印在上面,大家可以原諒對方嗎?」
在台上控訴『希伯崙』共生家園不當管教的,正是漢平爸爸,一談到患有自閉症的兒子漢平,遭到希伯崙以棍棒水管痛打管教,打到屁股青青紫紫兩大塊,甚至出現敗血症,幾乎是從鬼門關搶救回來時,就漲紅著臉,怒氣難消。然而漢平並不是個案,有輕度自閉症的阿文也和漢平一樣,也被到希伯崙棍棒伺候,阿文爸爸一回想起兒子自己逃出希伯崙,屁股一樣像兩塊木炭的瘀青,讓他和太太看得簡直難以置信。
「(原音)那大概過了兩天,老婆就發現,孩子在洗澡的時候,怎麼屁股上面就黑一塊那樣,然後我就把他叫過來,整個屁股拿下來看,就兩塊整個是黑的,那老婆當下就很驚訝,就問小朋友呀,那小朋友就說他被打了,那怎麼樣的情況,然後說他被打的時候,有一個人抓著他,另一個就在後面打,一開始用木棒,後來木棒被打斷了,就換鐵棒打。」
也曾一度也想將自閉症兒子送到希伯崙的監委王幼玲,回想起當時和希伯崙負責人溝通的過程時,似乎就已預見兒子一旦送到希伯崙將福禍難料,因此緊急踩了剎車。
「(原音)曾經我的孩子在情緒行為非常嚴重的時候,找不到任何的機構,那時我也受傷,找不到任何的機構,那時也有人推荐這個單位(希伯崙),所以我們也特別到這個單位去看,帶了孩子也去看,但是我跟主持人談了一下之後,我就決定我們的孩子是不適合這裡的,為什麼,因為它是共生家園,所以它並沒有做機構的登記,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會跟主持人說,這個孩子他有情緒行為,那他在外面如果暴衝起來,他會對別人有一些推擠攻擊的行為,那主持人就說,那別人會給他一些回饋回應,那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也就是他會被打,如果你打人家,人家也會回來打你,就是用這種方式在協助建立這個規約啦,所以我就想我們的孩子並不適合。」
然而為什麼他們都考慮或選擇將小孩送到了一個未立案的機構呢?原因都是『無處可去』。王幼玲無奈地說:
「(原音)他為什麼會去那裡,就是父母真的實在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做安置,這真的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我想父母把孩子送到這裡,應該也是心驚膽跳啦。」

監委王幼玲說,這些家長考慮將小孩送到未立案的機構是不得已的選擇,因為實在是無處可去。(曾國華/攝)
送社區支持系統遭拒 轉精神病院噩夢一場
一談到無處可去,阿文媽媽就滿腹委屈,她自知小孩自閉症固著行為就是話比較多,因此無論是送到庇護工廠或是小作所,甚至日照中心,在管理上都會是一個麻煩,最後通通都只能打包回家。
「(原音)自閉症的孩子本來就會碎碎唸,然後他小聲的碎碎唸,然後一些學員就會說,老師他好吵喔,因為他們都是已經進去很久的學員了,如果我兒子是新進來的學員,不能接受他,就覺得說,老師,他很吵,這樣子,老師就覺得說他會尊重原本在這裡就讀一兩年的孩子,所以就會找我們家長來開會,就會跟我們講說,他這樣子,我們可能會尊重他們,不接受你們的孩子。」
然而在全日型機構不收輕度自閉症的個案情況下,阿文父母最後被迫透過醫生幫忙,將阿文送到了精神病院,卻沒想到發現阿文每天吃的藥都大有玄機,也讓他們再度經歷了一次震撼教育。
「(原音)我們私下跟醫師討論以後,醫生就說要讓我兒子住院看看,然後我們就想說就你住院住看看,結果那也是很扯咧,他給他服了五種藥,其中有三種是鎮定劑,一直睡呀,昏睡呀,我們去看他的時候,早餐也沒吃,午餐也沒吃。」
儘管對自閉症個案用藥有許多爭議,而阿文父母仍決定離開精神病院,但曾是他們最後希望的希伯崙仍讓他們失望告終。

十年至少搬家三次 永遠跟人說對不起
事實上,和阿文一家一樣,為了照顧有重度自閉症的兒子─喬龍,江爸也備受煎熬,除了因此姻婚破裂外,但真正的惡夢卻是喬龍動輒尖叫或有不關門在家裡裸著身子的固著行為,不僅引發鄰居抗議,甚至房東還因此寄出存證信函,要求他們搬家,讓他們連住的地方都成了問題,十年內就搬了三次家。
「(原音)我們為了他脫序的行為,尖叫啦或是偷人家東西,或是敲敲打打啦,聲音很吵等等問題,為了他至少搬了三次家,因為鄰居都不容許他,叫他要搬家,管理員也罵我們,說我們小孩子也不顧好,然後造成大家的困擾,就是為了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不被社會所包容諒解,外面的人真的很難知道。」

江爸拿著房東寄出要求搬家的存證信函,無奈地痛訴許多自閉症家庭根本連住都成問題。(曾國華/攝)
面對工作及照顧的壓力,最終江爸也不得不透過醫生幫忙,將喬龍送到以治療精神疾病為主的康復之家。然而這些年下來,江爸卻始終記得他到處去跟別人說對不起,那種沒有希望的感覺。
「(原音)就是住進康復之家後的一次,然後康復之家的老師說他有情緒問題在尖叫,叫我馬上掛急診,半夜十一點,叫我掛急診,去松德醫院,然後我就開車載著我的兒子去松德,路上我很難過,你沒地方去了,被趕出來了,然後把你送到康復之家了,你又有這個狀況,我開車載我兒子,我邊開,我邊罵他,路上停下來,我揍他,我邊揍他,我邊掉眼淚,我說喬龍,我兒子,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你可不可以乖乖地聽話,不要再大叫了,結果那次被綁了,在那邊住了半天,那是我唯一次在松德。」
不是不當管教就是被當成精神病治療,這群重度或輕度自閉症孩子的爸媽心裡有許多說不出的痛,然而這就是現實的狀況,他們進不了機構,卻又無力在社區中找到喘息或接納的空間。
對障礙者做不得已篩選是社工最痛

「(原音)學員:這個我覺得很簡單。記者:真的嗎?很簡單嗎?學員:我之前也有做過五排,這個都我做的。」
為了解第一線的狀況,我們親身來到了台北市的「中山工坊」。這間位於建國北路華廈三樓的日間小型作業所,學員正在組裝電燈開關線路。
明亮的空間只能接收二十位的身心障礙個案,戴著眼鏡,相當熱心的社工員李昊勳告訴我們,當初台北市政府委外的人員配置就只有兩名教保員及一名負責行政事務的社工員,按照這種一比十的照顧能量,讓他們對於想進到小作所的障礙者真的必須進行「不得已」的篩選。只是一談到這種社工實務上的矛盾,過去曾是協助個案找機構的李昊勳,現在則顯得有些無力。
「(原音)就是我之前還在做中高齡心智障礙家庭服務方案的時候,我有些服務對象每天都吃藥控制情緒,那固著行為也很嚴重,或是說有很嚴重的收集廦,不要說小作所了,發展中心也不願意收,可能只能去精神科醫院松德啦,三總北投分院的社區復健機構,他們只能去那邊,那個時候我的工作,一部分就是想盡辦法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機構,願意收他們,或是告訴家長說你在家要怎麼教小孩,你要讓他吃藥,讓他行為比較穩定一點,才有可能有機構會收他,等到後來,我自己來接小作所來接機構的時候才體會到,有些服務對象我真的得要退掉,要不然第一線的教保員,甚至連我自己下去帶都還是不夠,就是負擔會整個炸掉,現場會整個炸掉,這是我感慨最深的啦,就明明是同一個孩子,原本以為我換了一個角色,好,你們機構不收,那我自己接機構,我自己收嘛,但還是不行,我們現場會炸掉,就是人力不夠,你一個比較重度的服務對象進來,可能要一個教保員整天跟著他,照顧負擔會非常重,可能那個沒有顧好,其他人也沒顧好。」

中山工坊社工員李昊勳接受訪問時說,經費人力不足,讓他們不得不對障礙者進行不得已的篩選。(中山工坊/提供)
事實上,這種「不得已的篩選」在庇護工廠更為「嚴格」,李昊勳觀察,原因不外就是庇護工廠在營運上必須自負營虧,因此員工的工作能力及速度如果跟不上,那也就只能說再見。
「(原音)基本上就是他們的能力要達到庇護工廠的要求,他們雖然有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的補助,但他們那個補助,不像我們工坊,他們等於是一個營利單位,自己賺錢,所以你在營利單位工作,你的工作壓力就很高,譬如說,庇護工廠就跟我們一般工廠一樣,就是整天都在工作,所以最基本的就是第一個,他們必須要有整天工作的體耐力,再來呢,譬如說,年節,三節,中秋節,父親節,他們要趕工,庇護員工就必須要受得了臨時趕工的大的工作量,還有品質的要求,所以最基本的就是,體耐力還有工作能力,要能達到可以出去賣錢的水準。」
無處可去 90%自閉兒畢業後只能家中坐
而我們實際打開台北市社會局網站,以首善之區的台北市為例,全部也僅有二十個小作所,總計名額僅有四百個,如果個案不出狀況,就能一直「工作」到六十五歲。但根據教育部統計查詢網的資料顯示,以一零八學年(2019年)為例,光是台北市特教學校畢業的高中職學生就有174人,這還不包括在一般高中職中的特教生,在在凸顯了支持系統進入社區的嚴重不足,也難怪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九十的自閉症個案在離開學校後,只能留在家裡,甚至出現社會功能退化的狀況。長期在第一線服務礙障者的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呂雅嵐說
「(原音)百分之九十沒有錯呀,因為沒有這麼多的小作所給他們去呀,你一年畢業是幾百個人嘛,你一間小作所收二十個二十五個而已,你根本沒有地方去嘛,所以他們就會在社區呀,那有些沒有地方去,長期下來,確實會有退化的狀況。」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主任呂雅嵐說,許多礙障者最後無處可去就只能留在家裡,社會功能因此退化得相當快。(曾國華/攝)
只是小作所難道不能多設一些據點嗎?李昊勳無奈地點出了問題的癥結。
「(原音)我們補助經費人力是一個社工兩個教保員,但是我們在第一線,所有第一線的人都知道,二十個服務對象至少要三個教保員才能顧得了,反正不管怎麼說啦,一個機構三個人是顧不來,一定要四個人,那這樣就會變成你所有的小作所一開張,就會先虧一年的人事費將近五十萬,所以機構都很缺,但大家都不是很願意或是沒有辦法去開這樣子,一個中小型的社福團體你可能一整年總預算可能就一千萬或是幾百萬而己,你怎麼去經營一個一開張就一年虧五十萬的單位。」
這就是典型自閉症個案發生情緒障礙時反應,一般人面對星兒的尖叫及撞牆,的確很難接受,也讓自閉症家庭面臨了極大的壓力。談到「被拒絕」,城城的媽媽,也是中華民國自閉症權益促進會的秘書長林娟圩感觸很深,
「(原音)我們是從日照開始,因為我們基本上去小作所也是會被拒絕,小作所它會希望孩子可以安靜至少四個小時,因為所謂的小作就是四個小時是做事,四個小時是休閒,但我兒子可能做十分鐘就很久了吧,他就會起來走來走去,那就是去日照,那日照我去過幾個月,但因為孩子有妥瑞嘛,所以可能會講穢語啦,噴口水啦,那個在他們的照顧上當然就是很挑戰。(記者:所以是被拒絕)是,是一個被拒絕,它們現在拒絕的方式,不會說你不能來,但它可能會說, 媽媽,他可能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那它跟我這樣講的時候,那當然是一個拒絕呀,他可能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那裡?對不對,那你要告訴 我那裡,那如果沒有,那就是一個推嘛!」

談到被拒絕,城城的媽媽,也是中華民國自閉症權益促進會的秘書長林娟圩忍不住苦笑,感觸很深。(娟圩 提供)
居家服務時數 難滿足障礙者家庭需求
少了小作所、庇護工廠及日照中心的支持,娟圩只能選擇居家服務,只是有限的時數仍然很難解決她所面臨的問題。
「(原音)這些時數就可能是比較少,譬如說,臨短托1年365個小時,那居家服務因為是長照體系就看孩子的失能等級去看你的時數及比例這樣,那我的孩子居家服務一個月大概是49小時左右,那你看分配到每一天裡面,一天是多少,那就是很不夠用嘛,那就是一天兩小時,兩小時?以我也是在職場工作的話,要去開會,我至少須要四小時,我出去交通一小時,回來交通一小時,我中間開會兩小時,還要很節制地開,不然的話有時還沒結束,所以這個時數,絕對大大不足以支應它的生活這樣。」
社區支持系統的不足,讓部分家長不得不求助全日型機構,然而相同的狀況卻也發生在機構裡,在機構及去機構化間,他們究竟該何去何從 ,我們在下一集將會為您持續追蹤報導 。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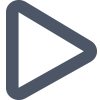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ti 中央廣播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