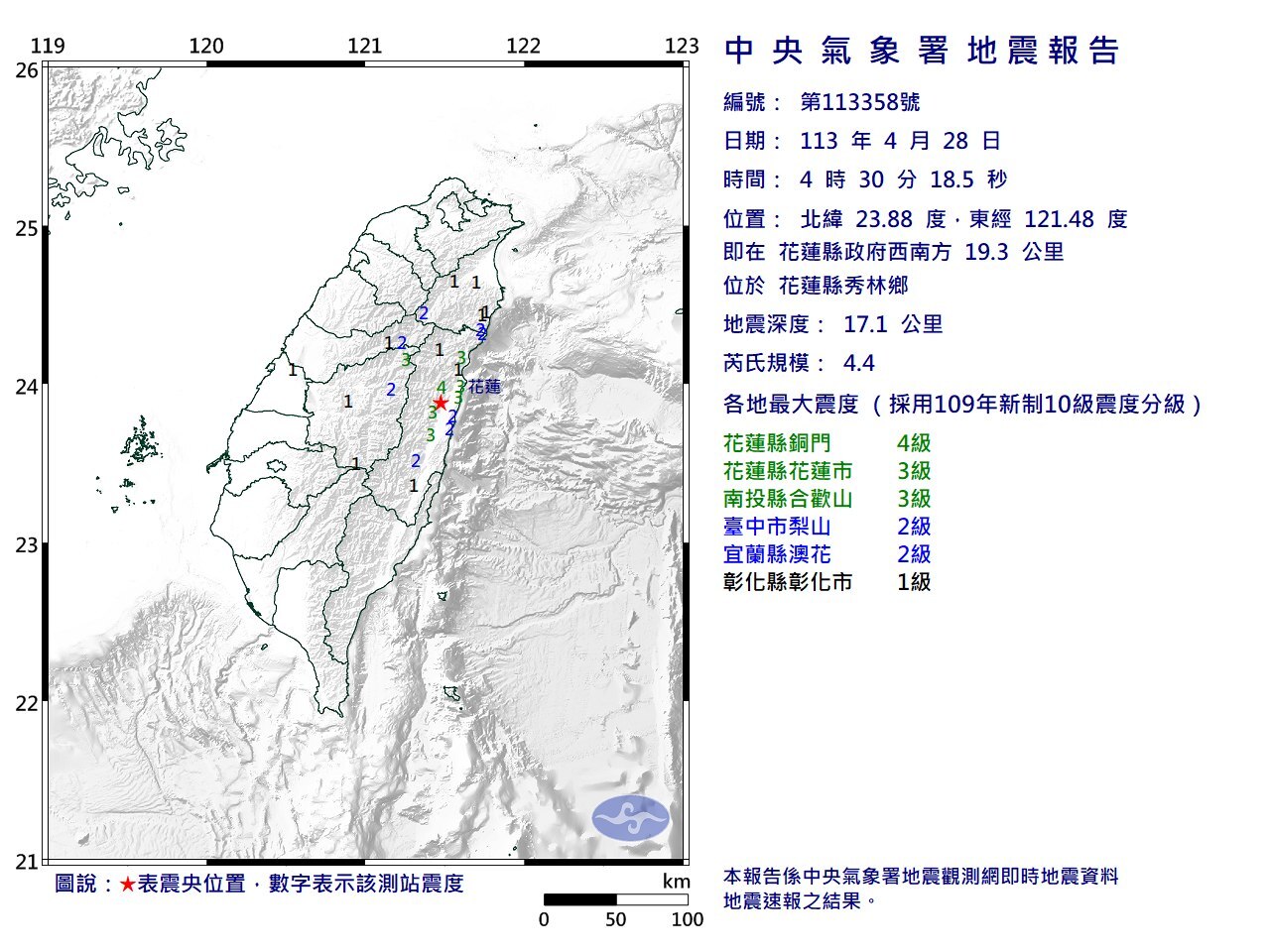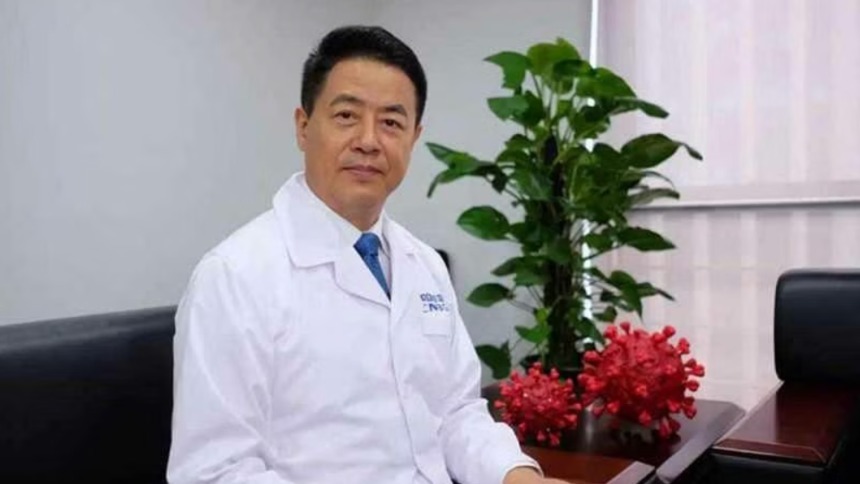向莉:何楊先生,請您談一談您之前在中國的生活和觀念的一些變化。
何楊:我是 1970 年出生在北京,我的童年、小學、中學沒有任何色彩,是灰暗的,特別灰暗。我出生一個幹部家庭,我是外交部子弟,算是一個相當優越的生活環境,但是在心靈成長過程之中是備受摧殘的感覺。我小時候比較瘦弱,經常被欺負,家庭沒有傳統的溫馨的感覺。因為從小就生活在寄宿幼稚園,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所以就從小缺乏父愛母愛的關照,在最需要父母的時候,他們也都不在身邊。因為我父親是一個外交信使,三個月才回家一次,所以沒什麼太多的感情聯繫,教育方法也比較粗暴,所以就沒有什麼交流。我是獨生子,一直到高中畢業,我覺得在整個青少年時期,感覺人生沒有開始,或者是地平線以下的一種人生。我媽媽是一個文藝青年,從我小時候起,她就經常給我讀一些文學名著,所以我有文學的基因,特別喜歡閱讀。文革 1976 年才結束,我 1970 年出生,經歷過文革後期,所以我沒能通過學習得到個人素質訓練的方式方法。說到轉變,是我在二十五六歲以後,我開始慢慢接觸紀錄片之後。我曾在中央電視臺的紀錄片部和北京電視臺「第三只眼睛」紀錄片頻道工作,在工作期間,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這種方向開始還比較模糊,就認為紀錄片是比較真實的,我喜歡這種真實的記錄。但是中央電視臺放映的基本上是宣傳片,它不屬於紀錄片的範疇。嚴格來說,北京電視臺的第三只眼睛才是一個生活紀錄片頻道,所以我就能夠接觸到一些底層生活和比較真實的紀錄影片。
何楊:那個階段(1995 年至 1998 年)中國第一批獨立紀錄片開始出現。他們主要受到了日本小川紳介的影響。以前紀錄片攝像設備都比較龐大,只有機構才能擁有,比如電視臺或者製片廠才有這樣的設備。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小型化的攝像機出現了,第一批的小型攝像機叫掌中寶(也叫超 8 ),這時候就出現了獨立紀錄片人,技術帶動了行業的發展。我非常佩服第一批紀錄片人,他們讓我接觸到了真正的紀錄片。這些獨立紀錄片人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胡杰。當時我在第三只眼睛擔任責任編輯,當時也向社會徵稿,我負責審核,於是看到了胡杰送來的的一部紀錄片。那是一部他拍的在海邊的紀錄片,一部非常簡單但又極為震撼、真實的紀錄片,記錄一家人在海邊艱苦求生的生活。他的鏡頭充滿了張力,沒有任何的虛實、沒有任何的技巧,甚至我們感覺他是沒有受過訓練,但是特別的真實,特別打動人心。一個長鏡頭下來,冬天人們在海裡頭撈凍菜。他的鏡頭讓我記憶猶新,我就結識了胡杰這個朋友,後來他就成為我一生的摯友。胡杰成為我的老師之後,他拍攝了《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紀錄片,當時他的初稿只有 30 分鐘,因為他要向很多受訪者介紹他要做什麼樣的紀錄片。當時的他採訪的這些右派和受難者都有一些顧慮。在經過中共的各種打壓之後,他們心中有深深的恐懼,他們不知道你拍攝這個東西是要幹什麼用的。所以胡杰就把僅有的資料剪輯了一個 30 分鐘的版本,想要告訴這些受訪者他想做什麼。我看到了那 30 分鐘的版本之後,覺得非常震撼,其實我真實的人生是從這一步開始的。
何楊:當然我也有一些文學基礎和理論儲備。比如,我大量的閱讀了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別處》。米蘭•昆德拉的這種寫作方式和他表達的主題也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有了閱讀量的積累和理論儲備之後,再看到中國的歷史上,竟然還有這樣的英雄存在。因為我們覺得中國這個時代已經沒有英雄了,不知道竟然有林昭這種自我犧牲、敢於面對暴政、敢於直言的人物,心中大受震撼。於是我就開始向胡杰學習,拍攝一些糾偏的紀錄片。當我們知道真理所在的時候,當我們知道真理在哪裡後,還有一步就是實踐真理。大部分人沒有這種實踐能力,就是說有很多人認識到了真理,但他不願意去實踐,不敢去實踐,恐懼戰勝了他們。由於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壓制了我們表達真理的渴望,比如說體制的限制,生活、家庭方方面面的限制。這在生活中占很大的比例。我其實是一個很膽小和懦弱的人,從小生活的經歷,並不具有勇敢的氣質。但我的負擔比較小,我覺得我已經是在地平線以下了(心理狀況)。我們需要反抗,有一種強烈的反抗欲望,反抗我們生活的環境、反抗教育、反抗所有對我們自由進行迫害的東西。從林昭的身上看到了我們有反抗的可能,這就是開始,是巨大的轉變。從這部紀錄片開始,我結識了一大批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們生活都非常貧苦、非常窘迫,但他們一直在實踐自己的理想。比如獨立紀錄片人,他們沒有任何的資金,他們拍攝的過程都非常窘迫,稍微籌點錢就去買磁帶,當時都是用磁帶(錄影帶),一盤磁帶也挺貴的,他們也沒有什麼收入。而北京電視臺第三只眼睛能支付他們一些稿費,採用他們的一些片子,我覺得這個工作非常有意義。其實我的那個工作非常短暫,大概兩年時間,但我在工作期間結識了第一批紀錄片人,結成深厚友誼。當時他們沒有說要去拿紀錄片去換個錢、得個獎,當時都沒這概念,好像就覺得看到了這樣的事情,就必須把它記錄下來,他們有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於是也就激發了自己成為一個不平凡人的渴望。以前我就庸庸碌碌地活著,覺得沒有選擇,當我看到他們的時候,就覺得人生其實是有選擇的。當我看到他們紀錄片中的人生,看到那些震撼人心的鏡頭,就願意投身到這樣的工作裡頭去。

何楊在福州街頭拍攝《赫索格的日子》(向莉提供)
向莉:大學你學的是什麼專業?你的第一部紀錄片是什麼?在做紀錄片的過程中,你覺得你做的哪些紀錄片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何楊:我在北京電影學院學編劇,要寫大量的文章,那時候沒有想自己會成為導演,因為我不知道。我拍的第一部紀錄片名字叫《被遺忘》。這其實是一組(7個)人類學紀錄片,我在西雙版納的一個艾尼族村莊裡頭,斷斷續續拍攝了三年,然後剪輯,雖然並不成熟,但對我是一個巨大的鍛煉。這部紀錄片跟土地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展現這個村莊隨著所謂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之後巨大的變遷。以前傳統的社會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進來,但又沒有建立起新的道德規範和家庭模式。尤其是他們沒有中原文化的傳統,儒家的基礎很薄弱,沒有漢族文化的積澱,其實就是從原始社會直接就跳到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新進來的東西很容易就把那裡的上層建築給推翻了,推翻了以後產生了大量的悲劇。比如以前有很嚴格的家庭道德標準,比如如何處理通婚通姦和家庭暴力。並且祖父輩和下一輩的這種關係紐帶全部斷裂,也產生大量的悲劇。我的那部紀錄片就是記錄這個村莊的變化,他們怎麼去婚喪嫁娶、離婚、打架,各種各樣的悲劇。人們的苦難都寫在臉上,就是沒有辦法去解決。因為這是我的第一部紀錄片,所以特別缺乏方向感,不知道怎麼表達,只是把過程記錄下來,它並不是很成功,但是確實是邁出了第一步,並且我在技術上有了一次很大的鍛煉。
何楊:對我影響最大、最震撼的一部紀錄片就是《吊照門》。2009 年當時胡杰介紹我認識了滕彪,然後我就認識了更多的人權律師。我當時還沒有什麼概念,只是想拍人權律師的紀錄片。2010 年劉巍和唐吉田兩位人權律師,要參加被吊銷律師執照的聽證會,他們邀請我去拍攝,這是我第一次拍攝和人權律師相關的東西,當天非常震撼!因為我從小是在恐懼裡被養大的孩子,沒有跟公權力直面打過交道,見員警都很害怕,躲著走。「不要惹事」,我從小的家庭教育就是這樣。但是那天拍攝的時候,有大批的訪民、律師、記者就圍在北京市司法局門口,有更多的員警在周邊,他們也在拍攝,在驅趕這些訪民之類的,我就拿著攝像機開始拍攝。你說害怕嗎?我小腿都在發抖,說實在的,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些。滕彪在街頭接受外媒的採訪,人權律師在討論案情,在說他們的經歷,那些訪民是那麼樣的熱情,當員警過來要查我身份證的時候,訪民就擋到我的面前保護我。當時我就想到六四時候的場景。六四的時候北京人是特別無私的,你看市民對學生的那種保護,我再一次體會到了人還可以這樣活著!這社會上竟然有這樣的人,他們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別人的權利活著和戰鬥,他們敢於在大街上批判政府,敢於指責司法不公。我想,天哪!他們怎麼能夠敢這樣呢!然後就有一種想認識他們的渴望,他們就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就這樣進入了維權界,開始不斷的接觸到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另外一個世界,一些被掩蓋的真相,一些苦難,還有人權律師的犧牲,一步步的,非常鮮活,那種感覺像帳幕被打開以後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

何楊 2011年3月24日被失蹤釋放後的照片(向莉提供)
何楊:胡杰是我的老師,我是他兒子的老師。胡杰的兒子在北京,也想拍紀錄片。他特別能吃苦,他曾經去一個大廈當保安,去體驗生活。他說,他住在地下四層,然後我們就策劃一個紀錄片的選題,我覺得非常難實現,但這個紀錄片的構思就成為我的一種夢想或者想要表達的。可能這個用紀錄片不太容易表達,或許電影可以更清楚地表達,就是一個立體世界。其實我們生活在一個立體的世界之中,但是我們認識不到這個立體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地下五層可能是垃圾房,他住在地下四層,地下三層、地下二層、地下一層是停車場,停車場上面第一層是那種大商場的珠寶店區域,第二層是超市和高檔專賣店,三層以上是咖啡廳、高級餐廳,四層以上就是高級公寓。這個社會、這個大廈是由各種利益體構成的,而這些保安只有在上班的時候、休息日的時候才能到地面上,他睡覺是要到地下去的,這就構成了一個立體的社會階層。我們的紀錄片是要記錄這個立體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平面的社會。但是我們其實生活在一個平面的社會之中,要不然在雲上生活,要不然在地面上生活,要不然在地下生活。但人們經常互相不認識,比如在 20 層以上高級公寓的人,不認識住在地下四層的保安,保安更不知道住在20層的他們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這正是我所構思的紀錄片的題材,每一層找一個典型人物記錄他們的生活,同時進行對比,但這只是一種構思,不容易完成。但其實它反映了我們紀錄片的職責是什麼?要構建這個立體的世界,讓不同階層的人都能看到對面生活的人的狀況,這樣才能產生同理心,才能產生一個真實世界的一個整體結構這種印象,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是一個真實和圓滿的世界,這就是紀錄片的責任。拍攝人權紀錄片讓我看到了我們立體世界的另一面,這是常人看不到的,所以我們(紀錄片導演)的社會責任就是把另一面掀開了給公眾,讓大家來看看我們這個世界的另一面到底是什麼樣的。那些國保(秘密員警的一種)說:「你為什麼老表現黑暗面之類的?」這種說法,都不值得駁斥。我說:「那你們的中央電視臺,為什麼天天表現那種光鮮的一面?你不去表現,還不讓我去表現?我們的分工不同,職責不同,你為了你們黨去做喉舌,那我為平民去發聲,有什麼錯?」這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感。當你找到了社會的定位和你感覺到你做的事對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時候,自信心也就增強了,人格也就完善了。
向莉:拍攝《吊照門》對你來說非常震撼,也改變你的價值觀。後面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何楊:然後我拍攝了《應急避難場所》、《赫索格的日子》,還有一些訪民故事等等。這些紀錄片,短片、長篇都有,我也就進入了國保的視線了。我就開始被國保喝茶,被軟禁。 2010 年,短短一年裡我拍了三四部片子,非常快,非常迅速。因為它不像其他的傳統紀錄片,需要長時間的記錄,你沒有時間,因為你必須要儘快的拍完、上傳、播出去,這是唯一的職責,來不及想到任何別的事情。因為你很快就會被掐滅,如果不儘快完成,這部紀錄片就完成不了了。一旦被官方知道了,他一定要在中途就把你給掐斷,所以必須儘快完成。所以那些紀錄片都非常粗糙。但我也不遺憾,因為我不是在拍文藝片,我也不是為了電視節預備這個影片,我只是要讓公眾知道真相,就像一個新聞記者的職責是一樣,所以很粗糙,像《應急避難場所》前後用了十幾天的時間就完成了拍攝,但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當時的國內國外的很多媒體都進行了報導,然後倪玉蘭這個人也就出現在公眾視線之中,大家就瞭解了她的故事,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些成就感。但它帶來的後果就是被官方列入黑名單了。 2010 年至 2011年,一年中有將近半年的時間都是被國保上崗的,被軟禁在家的,我也會被他們帶出去被迫旅遊等等。這個時候,我處在亢奮階段,一直在戰鬥。像拍《赫索格的日子》的時候,我們在街頭進行抗爭,大量的記錄,就跟政府開始直接的對衝,這種對衝的結果其實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衝擊和亢奮體驗。我是一個心理很脆弱的人,這就像腎上腺素密集分泌的一個階段,雖然在鬥爭之中,非常的興奮,但其實也特別傷人。就是經歷這樣長時間的軟禁、迫害、跟蹤騷擾,包括抓捕抄家,兩次抄家都是幾十個員警到我家來抄家,然後我被抓走等等。我見證了大量的苦難,這種苦難是世人不可見。那種苦難就是人處在黑暗的地獄之中,很容易產生心理抑鬱。如果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還能保持平常心,那說明他的心理太強大了!

《應急避難場所》何楊與倪玉蘭律師合影。
向莉:你在茉莉花革命時期也被抓捕了,請講講你那個時期的經歷。
何楊:茉莉花革命期間,我住在西直門。我和滕彪約一大批人吃飯,有一些人權律師參與,然後準備去東師古營救陳光誠。當時我們的電話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也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比如約在一個地方吃飯,基本上就是吃不成的。一次,我跟滕彪約了一個地方吃飯,然後滕彪就說,那個餐廳被關門了,國保去把那個餐廳關了,不讓我們吃。然後我們就臨時決定去西直門大街上走走,到了這個飯館就進去點菜。先點一桌菜以後,再打電話通知大家來吃,那他就沒法關門了,尤其是火鍋,又不用炒。於是菜點齊了,火一點上煮魚頭火鍋,一下我們就來了十幾個人,我們在裡頭吃,外面就一桌國保,是北京市公安局國防總隊的一幫國保人員。吃到差不多快結束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抓人,當時我還拍攝一些素材,像江天勇他們聊怎麼去營救陳光誠,大家有什麼想法什麼……結果我一到家,國保就把我的攝像機抄走了,把錄影帶什麼的全拿走了,到現在我也沒拿回來,之後就開始抓人。首先是唐吉田被抓走了,然後是江天勇、滕彪都被抓走了,然後挨個抓了不少人,但是一直沒抓我,但我被軟禁在家裡,之後是國保把我帶到了東北去旅遊。我被旅遊了十幾天,回來後還是軟禁。我以為他們不會抓我,因為他們當時說茉莉花的事,我其實沒有直接參與。但有一天,我忘了日期了,當時很多人權律師已經被抓進去一個多月的時間了,我夫人下班回家跟我說:「你是不是又惹事了?」我說:「我沒惹事,我不是在家裡嗎!他們天天給我關在家裡頭。」她說:「外面全都是小平頭。」我一聽就知道他們要抓我了。我就開始準備銷毀電腦檔,當時也是傻,怎麼就沒提前銷毀?可能就是僥倖心理,以為他們不會抓我。但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有人敲門。我問:「哪的?」他們說:「是物業的。」我說:「你別騙人了,你們是公安局的。」我丈母娘當時也在家裡頭,不讓開門,我說:「你別不讓開門,都把門砸了,以後我還得自己花錢修門。」我把門打開,一下出來衝進來 20 多個人,把我綁架到樓下。一下樓,我傻眼了,社區裡全是無牌照的車,我不知道有多少輛。我說:「這是抓恐怖分子?我需要這麼大規模的抓捕嗎?」當時我被戴上黑頭套,被運到一個秘密基地裡。我被關了6 天,整個茉莉花期間我可能是被關時間最短的一個。
向莉:為什麼您選擇流亡到美國?
何楊:在茉莉花事件之後,我已經不能再工作了。國保基本上全天候的跟著我,所有的事情都被限制了,也沒有辦法再拍片子。其實我的創作土壤已經喪失了,這個跟監禁沒有太大區別。有一次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他們講到一個移民途徑,就是傑出人才移民。我查了一下,我符合條件,就向美國申請了傑出人才移民,很快對方就批了。在此之前,我們一家人都沒有來過美國,但有一些朋友在美國。之後我們很順利的來到了美國。初到美國的時候,我經歷了一個比較戲劇性的一個過程。因為我長期處在抗爭第一線,心理上已經受到很大的創傷,而我自己在國內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到了國外之後感覺比較明顯。這就是我的身體突然放鬆下來了,而我的心還沒有離開中國。雖然身體已經在美國,美國是非常美麗,特別自由的,各個方面都感到很新鮮,但我的心、我的眼光還在國內,我還在不斷的在刷Twitter,還在跟國內的朋友們進行交流,看到的都是苦難,尤其是在 2015 年709大鎮壓的時候,看到我以前的戰友們都被抓了,這麼多人在監獄裡頭受到酷刑,所以仇恨日益累積,產生了嚴重的抑鬱後遺症。
何楊:為什麼叫後遺症呢?因為在國內的時候,我雖然有抑鬱症,但症狀不太明顯,因為始終處在一種高度亢奮狀態,每天都想著怎麼跟國保鬥智鬥勇。但是在到了國外,一放鬆以後,這種症狀就出來了。我看到的太陽是黑色的,是真正的黑色。在美國這麼一個美麗的環境下,我看到的太陽是黑色的,看到所有東西都是灰色的,沒有色彩的,心中充滿了仇恨、苦獨。這種症狀最嚴重的時候,我的夢想就是,我怎麼去給施加酷刑的人施加酷刑,我要報復回來。那時候,我天天想這些,我處在地獄的最深谷底,被仇恨所吞噬的心靈是多麼的苦,是多麼的痛,我是經歷過的。感謝主!後來我到了教會,心靈才真正得到了安慰。神從懸崖邊把我拉回來了!
向莉:我也有過同樣的感受。流亡泰國的時候,我被出賣,還被獄警苛責和處罰。我無法入睡,整夜地詛咒那些壞人。是神把我拉回正常的生活。
何楊:對!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神的安慰。在信仰之中,才真能感到這種安全和幸福。有了信仰的力量之後,人就慢慢變得健康起來,疾病慢慢得到治癒,心靈也恢復健康了。在普林斯頓地區,我們屬於中低收入,但是生活非常幸福。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人生是這麼的美麗,我的孩子,我的夫人也都慢慢得到了治癒,他們也是心靈受到了極大的創傷。我們的教會非常的溫暖,提供了無微不至的幫助。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人是這麼的可愛,在教會之中我們感到人是那麼的可愛。因為你跟那個罪惡的一方作鬥爭,時間長了以後,你會被同化的,你如果沒有堅定的信仰,往往你也會化身為魔鬼。我現在的生活就是充滿了喜樂和平安。感謝主!
向莉:您到美國之後,生活怎麼樣?您到美國之後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生活有何變化?
何楊:我還是從事人權工作,但不是那種急功近利、想要達到一個特別鮮明的目標,而是行公益,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這是神教導我們行使我們該有的、作為公民的義務和良知,不違背我們的良心去做事,並且為社會公益做出一些貢獻。最關鍵的是我已經喪失了任何的名利之心,我也不會去追求金錢和名利上的所得。每一件事都順其自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自從心裡平靜下來之後,我沒有再做任何的長紀錄片,全是一些短紀錄片,甚至有的不署名。但感覺到在這種敞亮的心態之下,我的作品的層次比以前高了很大一截。流亡美國之後,受洗歸主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生命得到了徹底的更新。我慢慢的平靜下來,其實這也是個治療的過程。到現在為止,我也沒有根除那些後遺症,也就是戰場應急症。有的時候,聽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在家裡會突然的暴怒,情緒失控,有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大部分時間,我的心裡充滿了陽光,覺得生命特別有意義,也特別快樂,我的朋友們也能感受得到。教會對我的幫助是最大的。其次就是我們以前的戰友們很多都流亡出來了,戰友們也都提供了很多的幫助。
向莉:您對後來的流亡者有什麼建議?
何楊:第一是要尋找到一個好的教會。我覺得靠我們人戰勝這個罪惡的世界是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靠神。在信靠神的基礎上,我們人也應該可以做點事情,當然也是在神的帶領下。其次,我覺得心理一定要健康。我們只有保持一顆健康的心,充滿愛的心,才能夠去面對這個罪惡的世界,而不能用苦獨去作為對抗。不要讓自己被它們同化,不要讓自己和那些魔鬼同流合污。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