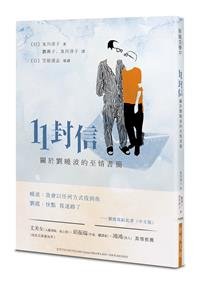
初見淳子
初見淳子,應是2008年3月。
章詒和先生的《往事並不如煙》前一年被譯成日文在川端幸夫先生的集廣舍出版。我陪章先生從大阪上京,一來去上野公園看櫻花,逛美術館,會朋友;二來參加關東方面的中國問題研究者與媒體人舉辦的該書研討會。
會後,照例在居酒屋小聚。淳子坐在不打眼的角落,熱心地為章先生翻譯。伊始,我誤以為淳子是遺華日僑的後代,用北京官話來說,淳子的中文說得「倍兒溜」。二戰後,遺留在中國東北(原滿洲國)的日僑有一百四十多萬人,戰後陸續回到日本。不過淳子是地道的日本人,她的家鄉在本州東北部的宮城縣,古時屬陸奧國的一部分,1600年伊達正宗於今天的仙台建造仙台城,市民愛稱其為「杜之都」,廣瀨川河畔、青葉山的鬱鬱蔥蔥使得仙台被翠綠包裹起來。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震災時距離震央最近的宮城、福島、岩手三縣遭到巨大的海嘯襲擊,宮城一縣死亡以及失蹤人數接近11000人。後來我聽淳子說,她的同學和親戚中好幾人喪生,很長一段時間,她都深陷巨大的悲傷之中。
那次會上還有矢吹晉教授同席。矢吹教授是日本著名的中國研究者,早在1989年即出版三卷《中國危機》;「六四」一週年出版《天安門真相》上下兩冊。2011年,他與加藤哲郎先生,淳子一起出版了《劉曉波與中國民主化的行方》(花傳社出版)。
淳子的論文後來結集出版--《現代中國的言論空間與政治文化》(禦茶水書房出版)─談的是關於中共黨內自由派李銳以及他周圍一直呼籲民主憲政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老幹部群體的形成,他們在歷史巨變中發揮的作用,與《零八憲章》的互動。淳子從高中就開始學中文,大學本科期間前往上海師範大學留學,純正的發音使得淳子成為NHK(日本放送協會)的電臺廣播學習中文的教師。2019年,天安門流血事件三十年祭,我們一起合作出版《用零八憲章學習教養中文》時,臺灣的年輕播音員育偉義務幫助朗讀錄音,使得本書成為一本既能學習中文,更能瞭解同時代的中國歷史與公民運動踐行現場的課本。
劉曉波與日本
2008年12月8日,劉曉波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的消息傳到日本,我正在大阪參加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的「懷德堂講座」,子安先生問我是否知道劉曉波?我告訴子安先生,2007年3月,在北京的萬聖書園,我同劉曉波見面的過程。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我研究中國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與流亡文學,一直關注被沉默、被遺忘的聲音。後來同留日學人一道創辦中日雙語文學刊物 《藍·BLUE》,主編日文部分,譯編《海外流亡文學》、《中國地下文學》專輯。2006年出版了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日文版(集廣舍)。那次我邀請川端先生等日本朋友一道去北京,廖亦武特意從四川趕來同我們見面,向我們介紹了劉曉波。
1989年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時,我在老家湖南,患肺結核住院治療。我母親幾乎每天來醫院給我送燉的各種土方子營養湯,告訴我學生與市民運動狀況。跟很多人一樣,我知道劉曉波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後期,通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選擇性批評-與李澤厚的對話》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審美與人的自由》,六四之後,《北京日報》刊登了一篇《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大批判文,後來印成小冊子分發大專院校當作思想教育的材料。
批判文引用劉曉波的話:「我從回國後,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我在天安門廣場同大學生度過了十幾個非常難忘的日日夜夜」。那時,對我們這些偏遠地方院校的師範生來說,出國留學,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好夢想,我們千方百計絞盡腦汁想辦法出國,他卻從國外跑回來螢火蟲撲火,真是不可思議。
在萬聖書園,曉波同我們談了整整一下午。書店劉老闆原是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劉曉波在秦城監獄(位於北京昌平,中國著名的關押政治犯的監獄)的獄友,經歷三年多牢獄生活之後,創辦了這家書店,現在已經成為北京自由思想與自由知識的地標。本書《11封信》中的第二封,就是給這位老朋友的信。
結巴子劉曉波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談到康有為、梁啟超、孫文流亡日本,談到支援中國新民主革命的日本志士,到當時的小泉政權;從他的家鄉日治時代的「新京」(今天的長春),居民享受的煤氣暖氣到日本人留下的基礎建設奠定了全國重工業基地,從七、八十年代中期自己這一代人親身經歷的外來文化的洗禮,尤其是日本電影《望鄉》、《追捕》、《生死戀》、《幸福的黃手帕》以及電視連續劇《阿信》、《血疑》、《排球女將》……,原來結巴子並不結。
那時劉曉波剛剛完成20萬字的《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其中重要的一章是《反日愛國的精明、懦弱和流氓》,他批評中國走火入魔的反日民族主義「已經可悲到弱智的程度」;同時他也對日本政府的只談「價格」,不談「價值」的對華外交功利主義也提出尖銳批評。
劉曉波說非常信任日本人的誠實。他舉了其中一例:1992年,北海道大學的野澤俊敬教授根據《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為底本翻譯出版了《現代中國知識人批評》(德間書店出版),但此時劉曉波出獄後回到大連的父母家中,外界沒有他的消息。譯者和出版社多方打聽找不到他,若干年後知道這件事後委託一位朋友去德間出版社詢問,出版社迅速將版稅如數送到他手裡,而且附帶一份言辭懇切的道歉信。曉波說歐美的媒體常常未經同意翻譯和出版他的文章,當然自己被封殺的聲音能夠由有心人翻譯傳到國外就已經非常感謝了,但是從未見過像日本人這樣誠實和守信用。
而幫助溝通此事的正是淳子和另外一位北京的朋友。
「萬聖」談話期間,劉曉波與廖亦武鬼鬼祟祟跑出去抽煙,嘻嘻哈哈一陣,回來後一臉正經地拜託我翻譯和出版他的書,說也許「牆外開花牆內香」。
六四之後, 劉曉波作為教師已經被剝奪講臺授課的權力;作為公民,在北京連暫住證都沒有,是「黑戶」;作為作家,除了香港、臺灣、歐美等少數華文媒體之外,在內地已經完全被消音,被蒸發了。
我告訴他,在日本,中國文學只是極為小眾出版,很難進入大眾商業流通的管道,遑論政論。即便有心人願意義務翻譯,出版社認同出版意義,哪怕非盈利地出版,版稅肯定是清湯寡水。劉曉波說,沒關係,跟老廖的書一樣的條件就可以了,賣得出去的話再結算,主要想聽到日本讀者對自己寫作的回饋。我非常理解對一個以保持獨立思考寫作為生命的個體而言,聽不到任何讀者的回饋之孤獨。
1949年之後以革命的名義公然焚書、禁書,作家被殺害、監禁、流放、罰以苦役,不計其數。大批知識人無家可歸,張愛玲離開上海之後三十三年,到去世都再未踏上故土;文革期間,音樂家馬思聰受盡淩辱,以偷渡的方式成功逃亡境外,並在美國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聲明。六四之後,中國知識人更是成批流亡,不僅僅是專制制度不容忍自由文學,更是自由文學無法容忍醜陋的專制制度。而劉曉波明白為表述的自由,唯有流亡,但又深知「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之切膚之痛,放棄了逃亡,成為在自己祖國大地上的「失蹤者」。
川端先生的出版社在九州的福岡。在日本,大東京「一括中心」,尤其在出版媒體方面,全國約三千家出版社主要集中在東京,東京以外的城市大概都可以被稱為「地方」,就像法國,似乎只有巴黎。
川端先生年輕時因為痛恨社會的不公,追求自由平等的民權,對「社會主義的中國」以及文革的浪漫幻想與共鳴而加入「中國書店」。林彪摔死溫都爾汗,六四時「人民解放軍」對人民開槍,「中華大一統」旗號下對弱勢民族的土地與文化的蠶食,像很多左翼知識人一樣,他的心臟連中機槍;以後他開始重新反思與調整自己的「中國觀」,在紙媒出版的困境中,仍然出版了很多有意義的書,包括王力雄、唯色、余杰等人的作品。川端先生向劉曉波表示,先找大咖出版社,如講談社、文藝春秋、新潮社、岩波書店,如果大咖出版社不肯出版的話,自己一定盡力。
緊接著,劉曉波的「轟炸」已經先於我的腳蹤炸滿了我的郵箱, 以後,他每每發表文章就打包「轟炸」我。但那時我仍專注於學院式的文學研究,有一搭沒一搭地回信,直到2008年12月他再度失去自由。
劉曉波的書在日本的出版狀況
子安先生從集廣舍的網頁上讀到淳子關於中國自由知識人劉曉波的連載,回到東京之後,立即同學術書店藤原書店聯繫。一個電話,我匆匆上京。在西泰志編輯的努力下,我主持編·譯《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本書是中日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晶。淳子除了翻譯劉曉波的文章之外,《零八憲章》,以及部分簽署者的《我們和劉曉波不可分割》,還撰文介紹《關於劉曉波》。
子安先生將在《序言》中指出:中共恐懼的是,劉曉波背負著天安門死者的聲音與支援《零八憲章》的生者的聲音,並且將二者合一。以後,子安先生提出「劉曉波,作為我們(原文「我們」二字加墨點以示重視)的問題」。
2009年藤原版的這本書成為諾貝爾和平獎頒獎之後,日本讀者比較完整地瞭解劉曉波六四之後艱難的心路歷程、思想與實踐以及《零八憲章》意義的重要讀本。
同年,子安先生與高橋順一教授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研討會,淳子和我都作為與談人參加。
2011年,藤原書店在其綜合學術季刊冬季號上推出《中國民主化與劉曉波專輯》,除了日本學者以及媒體人的文章之外,還翻譯了劉霞的詩歌;丁子霖、蔣培坤、余杰、徐友漁、王力雄、張博樹等人的文章。
後來集結成書《「我沒有敵人」的思想—中國民主化抗爭二十餘年》 ,書腰上話:「日中關係的未來在民間!真正的‘日中友好’是什麼?‘劉曉波’是我們的問題。忘卻天安門事件,是‘日中友好’嗎?為什麼‘親中’就不能批評中國的現行體制呢?長久以來的“親中VS反中”這種僵硬的二元對立思考方式囚禁了我們的對中認識,同樣體現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問題上。“天安門事件”究竟意味著什麼?《零八憲章》究竟意味著什麼?中國的近代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此,拷問對我們自身的認識與對於鄰國國民的應有姿勢」。
2010年11月,我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顫慄的抒情與慟哭的詩歌》評論,介紹劉曉波的詩與其生存美學—來自墳墓的訴說:「儘管十二年過去了,但那個被刺刀挑起血腥的黎明仍像刺刀尖一樣,紮進我的雙眼。從此以後,我看到的一切都帶著血污,乃至於我寫下的每個字的每一筆,皆來自墳墓中亡靈的傾訴」,(給劉霞的《承擔-給苦難中的妻子》)。
九州的另外一家文藝出版社-書肆侃侃房的老闆、詩人田島安江女史看到後找到劉曉波和劉霞的詩歌,與人合譯他們夫婦的詩集《牢裡的小耗子》。
曉波去世之後,我和田島女史合譯出版了劉曉波詩文集《隻身面對大海》,收錄了自1990年到2008年5月每年悼亡天安門受難者的詩歌以及散文詩《隻身面對大海》,劉霞的詩集《毒藥》。此外出版余杰的《劉曉波傳》日文版。
我們也許微力,但並非無力
2013年,大赦國際日本分部在東京與京都分別舉辦了劉霞的攝影展,並出版她的攝影集《沉默的力量》,淳子在本書中寫了一篇《霞姐》,「霞姐,年輕的朋友們這樣親切地喊。記得我們一起吃飯,電郵的來來去去中,我這樣稱呼她時靦腆的微笑。是的,靜靜的,有點兒羞澀的,總是那張笑臉」。
在劉曉波入獄,死亡,在劉霞不自由的日子,淳子不斷地在發出聲音。
這些年,淳子的主要致力於當代中國自由知識人的研究與翻譯。不久前收到她的新書《六四與一九八九—怎樣應對習近平帝國》(與石井知章教授合編·白水社出版)。
在日本,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關的研究與呼籲的集會上,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這些年,我的朋友們,或獄死,或流亡;或正在流亡的路上;或因為有損「偉、光、正」的光輝形象,不允許出境,或被吊銷戶口,成為在自己祖國的流亡者。
身邊的日本朋友,只要關注中國底層百姓的基本人權,公民運動,圖博特(西藏)或者東土(新疆)問題,就不被允許進入中國,或在中國遭到麻煩。
2019年,國立北海道大學的一名研究中日現代史的教授受中國社科院的邀請去北京,在旅館被帶走、拘留的消息震驚日本,尤其是日本中國問題研究界。
該教授在前一年還應中日韓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邀請,在近代史研究所做過研究報告,中國還出版過他的論文。
他並非「右翼、保守」派的學者,也不是「嫌中」、「反中」人士,他只是一名勤勤懇懇的學者。
儘管自2014年中國政府頒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以來,已經有十幾名日本人被拘留或被判刑,大都是公司職員,也有「中日友好協會」的人。前後也有在日華人學者的「失蹤」。只是未能引起媒體與企業的重視,也沒有企業與學界的溝通。
而這次,日本中國研究界的學者們終於發出抗議中國政治干涉學術自由的聲音。
也就是說,在自由民主國家的日本,以普世價值和客觀公正研究近現代中國,正在成為「高危」行業,同樣必須自我審查自己的思想與行為了。因為一不小心就可能踏入「敏感」區域,重者被扣上「間諜罪」,輕者不允許入境,田野調查和實地訪問無法完成,學術生命意味著終結。
淳子,只是默默地耕耘。她在大學開了一門關於「劉曉波」的研究課。
過去的十多年中,我和淳子多次在同一本書中,在同一次紀念會上「相遇」。
儘管我出國多年,但我的老父母仍在故鄉,成為我的牽掛;而在日本,關注言論自由,尊重人權,弱小民族的權益,很容易被貼上「右翼」或者「左翼」的標籤,研究與寫作只是孤立無援中孜孜前行。當我感到無力與哭泣的時候,淳子總是寄來一頁美麗字跡的信箋,「燕姐,我們也許微力,但並非無力」,外加一盒美味精緻的點心。
謝謝你,淳子,謝謝你同我們一起,在泥濘的路上,吹同樣風,淋同樣雨,謝謝你,與我們在這個時代「一期一會」,我們更懂得鄰人的意義,朋友的意義。
最後,我要深深地感謝好友MZ,謝謝你為本書(還有其他書)牽線搭橋,任何時候,你總是給我暖心的鼓勵和慰藉。正如淳子說的,從臺灣朋友身上,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濃濃的人情和貼心。
謝謝秀威出版社的理解與支持。
謝謝鄭伊庭,許乃文編輯,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雖然我們近在天涯海角,但仍能通過SNS對本書討論、斟酌。
感謝臺灣,倖存臺灣,中文世界不至於只有一種聲音。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