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27年前東非國家盧安達爆發種族大屠殺,百日內數十萬人遭人口占多數的胡圖族(Hutu)政府軍和民兵殺害;在大屠殺中,數十萬女性遭性侵,然而,她們所生下的小孩卻不被認定為倖存者,更背負「屠夫之子」的汙名,成長過程備受煎熬。
盧安達在1994年爆發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從4月初至7月中的100天裡,約80萬人遭到殺害,七成五的少數民族圖西族(Tutsis)人口在胡圖族政府發起的大屠殺下慘遭滅絕,其中受害者也包括溫和派的胡圖族人。
在整個國家殺紅眼之際,至少25萬名女性遭到性侵,加害者除了胡圖族政府軍和親政府的民兵組織「聯攻隊」(Interahamwe)外,許多是當地的男性,甚至是她們熟識的鄰居。在這場言語無法形容的殘酷殺戮後,估計有成千上萬名嬰孩呱呱落地來到這個世上。
但是,這些小孩卻生來就承受恥辱,他們是屠殺中遭性侵的女性所生下的後代,是「屠夫之子」。成長在大屠殺後盧安達社會與種族漫漫和解之路的他們,卻不見容於受害者和加害者兩方社群。
法新社報導,和在大屠殺期間失去雙親的小孩不同,這些因性侵而誕生的孩子們,並不被認定為種族滅絕下的「倖存者」;這也就意味著,他們無法得到那些專給予倖存者的特定援助,只能透過他們母親在大屠殺後從一項專門支持基金所得到的支持,間接受到援助;而面對生來即承擔汙名,更讓他們成長過程備受艱辛掙扎。
背負「屠夫之子」汙名 不見容於社會
現年26歲、使用化名、現於盧安達南部城市恩延扎(Nyanza)就讀會計的派翠克(Patrick)說,「我的心中有許多傷疤」。他說,「我不知道我的父親是誰,我的未來將一直都很複雜,因為我不知道我的過去。」
他回憶就學過程中,難以融入學校同學,日後這份痛苦還一直跟隨著他,他常因想起這段過往而陷入崩潰。
派翠克受到社會的嚴重孤立,曾讓他多次心生自殺念頭,第一次甚至是在理應無憂無慮的11歲。 他告訴法新社,「直到幾年前,社會都還因為我出身的歷史而沒辦法接受我。」「圖西族社會不行,胡圖族也無法,他們不在意我。」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在盧安達陷入血腥屠殺期間,至少有25萬婦女遭性侵。歷史學家指出,當中許多婦女淪為性奴隸,有些人被加害者故意傳染愛滋病(HIV)。
許多倖存者更從來沒有告訴過她們的孩子,他們是在性侵懷孕後出生;有些人則將過去深埋心中,未曾和後來結婚的男人分享自己所遭遇的苦難,就是怕遭到拒絕,無法建立家庭。
派翠克的媽媽奧諾寧(Honorine)當年遭到多次性侵,在大屠殺期間,她和多名婦女一同遭到一群胡圖族民兵俘虜,這群激進份子結束每天的屠殺後,回到屋裡強暴她們。
幾天後這群民兵逃至別的地區,奧諾寧試圖徒步回到北邊的家鄉和家人團聚,卻在途中再次遭到性侵,也在這次的性侵中懷孕。
儘管發現自己懷孕後,奧諾寧一直在否認的狀態下過日子,也時不時有自殺的念頭,但她最終仍生下派翠克,扶養他長大。時至今日,她仍把派翠克成長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怪罪於自己。她並說,在兒子成長過程中,她沒有對他展現太多愛,這也讓她一直備感罪惡。
奧諾寧之後結婚成家,但她的丈夫將派翠克拒之門外,並稱他為「殺手之子」。
屠殺未曾結束 性侵作為屠殺手段
歷史學家杜馬斯(Helene Dumas)指出,大屠殺中的性侵事實上帶有意識型態色彩,是種族滅絕的手段之一。
她對法新社說,「性侵被用作為貶低和消滅圖西族的手段。」「這些種族滅絕事件背後的人鎖定女性身體為目標,企圖對親子關係強加一項激進的毀壞,以讓任何女性都無法生下圖西族的孩子。」
她指出,這些遭性侵而出生的孩子們的存在,和發生在他們母親身上的事情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她說,在2011年,前家庭和婦女事務部長尼拉馬蘇胡科(Pauline Nyiramasuhuko)遭聯合國特設的盧安達問題國際法庭定罪,被判處終身監禁,理由是因為她在1994年任部長期間,煽動屠殺和性侵圖西族女性。
杜馬斯意味深長地指出,「這就是為什麼這場種族滅絕從未結束的原因。」
「把自己視作人」 心理治療小組助倖存者面創傷
殺戮後的盧安達在一片殘破中努力走上和解之路,不過在一開始,這些遭性侵的女性倖存者是如何面對她們的創傷經驗,卻很少受到關注。直到近年來,有些非政府組織開啟了這項重要工作,致力於協助女性處理和理解她們所受到的創傷。
心理治療師穆坎索羅(Emilienne Mukansoro)在全國帶領的心理治療小組是其中的例子。從2012年以來,穆坎索羅自願帶領全國9個心理治療小組。小組中的許多女性當年是在她們摯愛的親人和群體面前受到性侵,以及在過程中被蓄意導致傷殘。
現年53歲的穆坎索羅也歷經盧安達這段傷痛的歷史,她在當年的大屠殺中失去了父親、8個兄弟姊妹和其他家庭成員。過去18年來,她一直與大屠殺中的性侵倖存者工作,透過團體治療讓這些傷痛有一處安放之地。
現年46歲的瑪莎(Martha)是心理治療小組的成員之一,她感謝心理治療小組,讓她可以將自己視作「一個人」,也終於可以向她的女兒訴說,她是如何誕生於暴力中。
居住於該國南部穆漢加縣(Muhanga)的瑪莎說,當年她和其他婦女躲藏在森林中,但還是被民兵發現,遭到他們性侵好幾天。她在1995年生下她的女兒黛安娜(Diana)後,被她的兄弟們斷絕關係。
她的兄弟們當時和圖西族領導的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一起作戰,也就是後來終結大屠殺的力量。瑪莎回憶起一名兄弟在得知她懷孕後狠狠地說:「我是不會浪費時間在你身上的。就算妳死了,我也不會浪費時間埋葬妳。」
她的女兒黛安娜則是在9歲時,開始問起她出生時的狀況。瑪莎說,「我那時候告訴她『妳沒有爸爸,他死了』。」
瑪莎後來嫁給胡圖族人,再生下一女。當法新社在她被香蕉樹和尤加利樹包圍的家中訪問她時,26歲的黛安娜正幫她同母異父的16歲妹妹輔導作業。
黛安娜說,「我必須要面對我的爸爸是施虐者和殺手的事實。」她並說,在了解更多在大屠殺中遭性侵的女人們的故事後,像是許多女性選擇墮胎拿掉小孩,或將產下的孩子丟棄在森林中,她認為媽媽「非常勇敢」。
誕生於暴力之痛 盧安達社會和解的共同課題
然而,對於面對得知她出身而帶來的創傷,一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黛安娜說,多年來,她將媽媽和舅舅們斷絕關係的原因怪罪於自己。
不過,在她先前主動在社群軟體上創建一個群組,和她的表兄弟取得連繫後,她現在已經知道對於過去的那些錯誤,她是「無辜的」。儘管她的舅舅們還是不讓她和表兄弟們往來,但她期盼,有朝一日他們的關係可以修復。
而對於派翠克來說,在經過多年努力「接受」自己痛苦的過去後,他已經可以更自在的和他的朋友與同學分享他的故事。他說,「人們正慢慢的、慢慢的接受我是誰。」他並強調,盧安達社會的「和解」過程仍在持續。
盧安達大屠殺倖存者援助組織「記憶」協會(IBUKA)執行秘書阿希沙基耶(Naphatal Ahishakiye)說,要克服大屠殺的災難性後果,仍需要好幾十年的時間。
他說,「盧安達正在一天一天重建團結,然而,我們必須繼續讓民眾意識到,如何讓這些因性侵誕生的孩子融入社會。」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用Podcast訂閱本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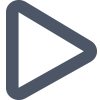 Rti 中央廣播電臺
Rti 中央廣播電臺 











